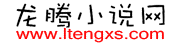另外三块是澄泥砚,也是四大名砚中的珍品。一块朱砂红,一块鳝鱼黄,一块蟹壳青,何松年拿拿放放,拿不定主意儿。老袁说:“这三方也是名砚,贵重着呢,松年,你随便挑选。”桂满堂见松年拿不定主意,说:“松年大哥,还是端砚吧,湖笔端砚宣纸歙墨最有名堂。”老袁的脸皮皱了皱,没言语。
选好了砚台,老袁说:“我这里有盒好墨,也是歙县的名家所制,正好跟砚台相配。”说着,翻出一个铁盒,铁盒上生了红锈,打开盒子,原来一组四块,分别刻着松、梅、竹、菊等草木花卉,图像温润清晰。何松年很高兴,看了又看,一时不忍释手。
老袁说:“松年大哥,你闻闻啥味儿。”松年捧在鼻子上闻了一阵儿,香味儿很浓,说不上啥香气,摇头笑了笑。老袁怪怪地说:“这里边有麝香、梅片、珍珠、槟榔,好几味中药呢,不招虫不霉烂,放一千年也是这样儿。做墨可是个工夫活儿,用料讲究着呢,上好的松烟、桐油、广胶和在一起,舂一千遍,揉一千遍,搅坯、翻凉、描金,下了模子,还要风干一百天。”桂满堂不懂这些,心说,干啥也不容易,啥事物也有讲究,文人墨客更不简单。
松年抱着端砚,桂满堂捧着歙墨,刚要出去,老袁又把他俩叫住了,说:“你俩稍等,我给车先生找个笔筒儿,我记得还有个好笔筒来着。”老袁在橱柜上找了一阵儿,拿出一截儿树桩,看也没看,抱着就出来了。
到了天井里,老袁对着太阳吹了几口,擦了一遍,笔筒的形状出来了。笔筒上疙疙瘩瘩,长满了像是葡萄又不是葡萄的树瘤。老袁说:“别小看了这东西,这是一截儿朱砂梅,上千年才长成这样儿呢。看见了吧,这东西叫瘿瘤木,也叫树猴儿,长得像葡萄,又叫葡萄瘿。你看这漆色,你看这包浆,多亮堂啊!”松年拿在手里,感激地说:“老袁,车先生泉下有知,没白教了你这个学生!”
老袁把一堆东西,封在一个纸盒里,刚要扎起来,老袁又开了纸盒,反复看了一遍,明知道老袁不舍,两人却不好说啥。桂满堂说:“哪儿有上好的石料?老袁,三番的文化物儿,都在你心里装着吧。”老袁说:“我领你们去个地方。”老袁只管在头里走,一路上不说不笑,何松年知道老袁心疼他的宝贝,故意落在后边,不让老袁看见他手里的东西。
走了不下几里地,到了城边儿上,老远看见一片树林子,林子很繁密,这会儿树叶落尽了,若在春夏,该是多好的一片阴凉!林子外边有一间孤零零的土屋,到了土屋跟前,荒野里堆着一大堆石料。老袁说:“这一片都是碑石料儿,这会儿生意冷淡了,文化大革命以前,多的时候,二十几个石匠呢。”
老袁推开了屋门,屋里只有一盘短炕,炕跟前挨着一个土坯炉子。老袁说:“老东西哪去了?”老袁伸手摸了摸炉膛,说:“没走远,老东西不知上哪去了。等等吧,一会就回来。”屋里阴冷,看起来老袁跟主家很熟,伸手从炕洞里摸出一只瓦罐,抱着喝了两口。
太阳从林梢子上掠过来,斜照进屋里,何松年摸出烟卷儿,三人抽了一会。桂满堂说:“袁大哥,你跟石匠熟?”老袁点头说:“这家石匠啊姓燕,燕子的燕,祖上鲜卑人士,这个姓在三番不多见,祖辈都是石匠营生。原先吧,我给他们写碑文,从他这里支一份儿工钱。到了文化大革命,他家的生意就完蛋了。这几年指望下乡,给老百姓掺磨,混个三核桃俩枣。老燕性子死犟,我让他上我那儿打扫打扫,给他俩工钱,人家说啥也不干。”
三人等了一会,慢慢磨没了耐心,刚要走,门口影子一闪,老袁忙站了起来,大声说:“老燕,看坟地去了?”门口站着一个瘦高老头儿,就是老袁说的老燕。老燕花白胡子,脸上却很红润,看不出多大年纪。
老燕耳朵背,看着老袁的嘴巴说:“今儿,俺爹忌日,上坟!”老燕穿着一个破大袄,半截袄袖子,露出黑乎乎的棉絮,看样子很长时间没见老袁了,老燕显得很高兴,从怀里掏出一只酒瓶,晃了晃,咬开瓶子,递给老袁,老袁仰头啁了一口,老燕笑了笑,又从破袄里掏出一小袋儿椒盐花生,一截儿薰肠。老袁摆摆手说:“行了老燕,别臭显摆了,留着你自己用吧。”
石匠老燕轮番看着桂满堂何松年的脸,也不问,也不说话,脸上只是笑。老袁大声说:“老燕!”老燕张着口,答应着,“啊?”老燕还是笑,指指自己的耳朵,意思是听着呢。老袁变戏法似的,掏出一瓶儿酒,两封点心,一包羊杂碎。桂满堂也觉得奇怪,没见老袁啥时买的呀。
老燕笑得更厉害了,两颗东倒西歪的门牙,在口腔里跳。老袁说:“老燕!”老袁指指桂满堂和松年,大声说:“他们啊,要做碑!”老燕笑着说:“好,好,做碑好!”老袁说:“你个老东西,跟你说话这个费劲儿!老燕,他们要上好的石料,有没?”老燕笑笑,指着门外边说:“要啥有啥,自己挑。”
老袁领着松年满堂出来,在石料堆里看了一遍。老袁说:“这些石料,都是几十年前进的,看出来了吧?看看,没炸纹,没土锈。松年大哥,你看中了哪块石料?石碑好做,一料难求,这做石碑啊,用的是大石整石,不知开多少山,才求出一块毛料来。”
选好了砚台,老袁说:“我这里有盒好墨,也是歙县的名家所制,正好跟砚台相配。”说着,翻出一个铁盒,铁盒上生了红锈,打开盒子,原来一组四块,分别刻着松、梅、竹、菊等草木花卉,图像温润清晰。何松年很高兴,看了又看,一时不忍释手。
老袁说:“松年大哥,你闻闻啥味儿。”松年捧在鼻子上闻了一阵儿,香味儿很浓,说不上啥香气,摇头笑了笑。老袁怪怪地说:“这里边有麝香、梅片、珍珠、槟榔,好几味中药呢,不招虫不霉烂,放一千年也是这样儿。做墨可是个工夫活儿,用料讲究着呢,上好的松烟、桐油、广胶和在一起,舂一千遍,揉一千遍,搅坯、翻凉、描金,下了模子,还要风干一百天。”桂满堂不懂这些,心说,干啥也不容易,啥事物也有讲究,文人墨客更不简单。
松年抱着端砚,桂满堂捧着歙墨,刚要出去,老袁又把他俩叫住了,说:“你俩稍等,我给车先生找个笔筒儿,我记得还有个好笔筒来着。”老袁在橱柜上找了一阵儿,拿出一截儿树桩,看也没看,抱着就出来了。
到了天井里,老袁对着太阳吹了几口,擦了一遍,笔筒的形状出来了。笔筒上疙疙瘩瘩,长满了像是葡萄又不是葡萄的树瘤。老袁说:“别小看了这东西,这是一截儿朱砂梅,上千年才长成这样儿呢。看见了吧,这东西叫瘿瘤木,也叫树猴儿,长得像葡萄,又叫葡萄瘿。你看这漆色,你看这包浆,多亮堂啊!”松年拿在手里,感激地说:“老袁,车先生泉下有知,没白教了你这个学生!”
老袁把一堆东西,封在一个纸盒里,刚要扎起来,老袁又开了纸盒,反复看了一遍,明知道老袁不舍,两人却不好说啥。桂满堂说:“哪儿有上好的石料?老袁,三番的文化物儿,都在你心里装着吧。”老袁说:“我领你们去个地方。”老袁只管在头里走,一路上不说不笑,何松年知道老袁心疼他的宝贝,故意落在后边,不让老袁看见他手里的东西。
走了不下几里地,到了城边儿上,老远看见一片树林子,林子很繁密,这会儿树叶落尽了,若在春夏,该是多好的一片阴凉!林子外边有一间孤零零的土屋,到了土屋跟前,荒野里堆着一大堆石料。老袁说:“这一片都是碑石料儿,这会儿生意冷淡了,文化大革命以前,多的时候,二十几个石匠呢。”
老袁推开了屋门,屋里只有一盘短炕,炕跟前挨着一个土坯炉子。老袁说:“老东西哪去了?”老袁伸手摸了摸炉膛,说:“没走远,老东西不知上哪去了。等等吧,一会就回来。”屋里阴冷,看起来老袁跟主家很熟,伸手从炕洞里摸出一只瓦罐,抱着喝了两口。
太阳从林梢子上掠过来,斜照进屋里,何松年摸出烟卷儿,三人抽了一会。桂满堂说:“袁大哥,你跟石匠熟?”老袁点头说:“这家石匠啊姓燕,燕子的燕,祖上鲜卑人士,这个姓在三番不多见,祖辈都是石匠营生。原先吧,我给他们写碑文,从他这里支一份儿工钱。到了文化大革命,他家的生意就完蛋了。这几年指望下乡,给老百姓掺磨,混个三核桃俩枣。老燕性子死犟,我让他上我那儿打扫打扫,给他俩工钱,人家说啥也不干。”
三人等了一会,慢慢磨没了耐心,刚要走,门口影子一闪,老袁忙站了起来,大声说:“老燕,看坟地去了?”门口站着一个瘦高老头儿,就是老袁说的老燕。老燕花白胡子,脸上却很红润,看不出多大年纪。
老燕耳朵背,看着老袁的嘴巴说:“今儿,俺爹忌日,上坟!”老燕穿着一个破大袄,半截袄袖子,露出黑乎乎的棉絮,看样子很长时间没见老袁了,老燕显得很高兴,从怀里掏出一只酒瓶,晃了晃,咬开瓶子,递给老袁,老袁仰头啁了一口,老燕笑了笑,又从破袄里掏出一小袋儿椒盐花生,一截儿薰肠。老袁摆摆手说:“行了老燕,别臭显摆了,留着你自己用吧。”
石匠老燕轮番看着桂满堂何松年的脸,也不问,也不说话,脸上只是笑。老袁大声说:“老燕!”老燕张着口,答应着,“啊?”老燕还是笑,指指自己的耳朵,意思是听着呢。老袁变戏法似的,掏出一瓶儿酒,两封点心,一包羊杂碎。桂满堂也觉得奇怪,没见老袁啥时买的呀。
老燕笑得更厉害了,两颗东倒西歪的门牙,在口腔里跳。老袁说:“老燕!”老袁指指桂满堂和松年,大声说:“他们啊,要做碑!”老燕笑着说:“好,好,做碑好!”老袁说:“你个老东西,跟你说话这个费劲儿!老燕,他们要上好的石料,有没?”老燕笑笑,指着门外边说:“要啥有啥,自己挑。”
老袁领着松年满堂出来,在石料堆里看了一遍。老袁说:“这些石料,都是几十年前进的,看出来了吧?看看,没炸纹,没土锈。松年大哥,你看中了哪块石料?石碑好做,一料难求,这做石碑啊,用的是大石整石,不知开多少山,才求出一块毛料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