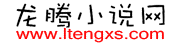自蒙古人的发祥之地三河源头一路向南,便是著名的大戈壁。中国的古人称之为“瀚海”,盖因其植被稀缺,平平漫漫,一望无际之缘故。起伏的沙丘则一如海之波涛,然则此物亦诚然随风而动,时常改变其形貌与位置。由细砂与碱性粘土所结构而成的地面坚硬如铁,拳头大的砾石遍布其表,缝隙中偶尔刺出数缕灰朴朴的蒿子和干巴巴的沙棘草,除此之外,再无任何生命的迹象。一旦阵风吹过,漫天黄沙腾空而起,遮天蔽日。那些肉眼不可分辨的粉尘,因风势狂飞劲舞,人类的感观亦因之变得凝滞迷朦起来。
至于风平沙静的时候,灰白色的炽烈阳光立刻将熊熊大火不断投向地面。不久后,戈壁就会变成一块变灼得通红的铁板一般变为赭石色。在这个时候,如果有谁敢于跳下骆驼背来,他的双脚立刻就会了解什么叫烧烤。高温压榨出地表上的每一丝水分,使之化为不绝的雾气,与几欲熔化的空气杂糅一处,不时在半空中发生着不规则地波动,干扰着人们的视线,使之变得扭曲变形,颠倒倒错。只有在清晨时分,才是一天中最为清爽明朗的时刻:天空挣脱出厚重夜幕的掌控,逐渐向靓丽的浅蓝色过度。不久后,晨曦的光剑刺透轻薄的雾霭,还光明于大地。那一刻,空气如山间溪流般透澈,轻快地流动于人们的鼻息肺腑之间,那感觉如丝帛般柔滑动人。视线如此悠远,可以无远弗界地延展向呈现出本色的天地尽头,近而使人辄生错觉:沿着这条路可以一直走到天上去。
成吉思汗选择的出兵时间是一年中穿越戈壁的最佳时机。来自西南方向的干燥季风未至,沿着骆驼商队所开辟的通道行进,可以不时在一些沙丘或风化严重的岩石背后附近寻到一些零星的草场,还有向地下挖掘不及两、三米甚至数呎便可涌出的清泉。有了这些休憩之地,蒙古兵马就绝偶无水草匮乏之虞。
在这里,偶而现出几间帐篷和数匹驼马的影子也算不得一件稀罕事。成吉思汗便多次亲眼看到过一些人影的晃动。这些为追逐利益而跋涉于生命边缘的人们从外表穿着上几乎全无二致。同样宽大的遮阳笠,袍子和靴子乃至稳健的步履,使他们个个都具备了孪生兄弟的特征,红褐色的砂地上驻留着他们长长的影子。这沙丘、岩石、牲畜、人形在红褐色的背景映衬下,表现极为生动。
一千多年来,每一年的这个季节和这条路,对于南方的农耕民族来说,都是相当危险的时期。成群结队的游牧民族长驱直入,出现在这条名为“河西走廊”的狭长地峡一带。再向东,是绿意盈盈的河套地区,日夜奔流的黄河在大地上划出一个大大的“几”字,将河套平原同河套以外的沙化草原一劈两半。穿越最后沙丘与盐池后,眼前的情景就因河流的走向而变得截然不同起来。
从中国古人留下的“黄河百害,唯利一套”的说法来看,这条中国北方最大的河流在此处还显得相当可爱,平静而温和地灌溉出许多草原和良田。因之而诞生的绿洲农业的富庶景象——绿树成荫、繁花似锦、果实累累、麦浪翻滚,对于刚刚走出荒凉戈壁的游牧骑兵来说,当真是如诗如画的仙境,富足安康的天国。从而激发了他们大肆掠略的热情,冷酷的铁蹄如入无人之境,困扰着历代中原统治者的心绪。
如今,这一困扰将由唐兀惕人来率先承接,而他们所面对的偏偏是千年以来各蛮族中最伟大的首领和最强悍的部队,这使得其宿命悲剧的色彩愈发浓厚起来。
唐兀惕帝国的首都名叫兴庆府(1),位于黄河大“几”字型的一撇之上,西傍贺兰山脉,东接鄂尔多斯草原,是一座典型的绿洲城市。经过二百年来的不断完善与开凿,在其郊区形成了四通八达的灌溉渠网,促进了这里发达的农业与良好的气候。同时,这也是一座属于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工商业城市。这一点,通过马可.波罗在其著名游记中所提及的大规模驼绒织品工场和同样巨大的交易量上即可窥见其当年之风采。
对唐兀惕人的征伐以斡罗孩城(2)之战揭开了序幕。负责驻守此城的唐兀惕人将军史称嵬名令公,是他率先发现了蒙古人的异常动向并立即将自己的判断上报于当时的唐兀惕王李安全。嵬名令公在奏章中指出:此次来袭的蛮族图谋甚大,绝非一般性质的劫掠,宜早图对策。
这位李安全(3),在中国历书中被称为襄宗,是于去年通过篡位的方式刚刚登上宝座的新君。按照他的年号为“应天”。因此,纪元1207年便是西夏的应天二年。从多方史书来看,李安全都不能算是一位昏君,而且相当有军事才能,即位之初也力图重振西夏之国威。在得到嵬名令公的奏章后,他立即命自己的世子李睍为主帅,以宿将高令公为副手,发重兵迎击。
他们在斡罗孩城与嵬名令公的边防部队会师后,双方迅速议定了战法。决定依托城防布阵,诱蒙古军主力前来决战。如果战胜,自不消说。若一旦不利,也可依托坚城,形成持久局面。根据游牧民族的特性,这种持久战是对方最难适应的,最终可导致对方耐性全失,不得不撤兵。届时,自后追击,可一举反败为胜。就其本质而言,这不失为一种攻守兼备、稳健合理的战法,唐兀人本身便是游牧民族的后裔,只有他们才能想到如此具有针对性的策略。这一切的计划都构架于斡罗孩城控河套要冲的险要位置之上,无论任何来自北方的入侵,都必须通过此地才能进一步染指南方的绿洲,除非敌军愿意横渡东面的黄河或不惜穿越西边的巴丹吉林沙漠。
“世子请安居城内,看末将与嵬名令公破敌。”
在高令公以此言做为整个军议的结语后,李睍点头承知。战场对于这个仅有十余岁的少年而言,确实是一件难以理解的事情。做为提升士气的标志,他能亲临前线已经完成了主要的使命。其父李安全在临出兵前已经对其职权做出了严格的规定:不得绕过前线将领发布任何指令,避免干扰将军们的战场指挥。从李安全的本心出发,他很希望自己亲自出阵,然而他必须留在都城内应付那些对自己的权威尚存异议的亲戚和臣子们。可见,篡位者的日子并不好过。
西夏军按照预定的战法在斡罗孩城下严阵以待,然而一连数日,却连蒙古人的影子都未发觉。根据远近斥候传来的消息,方圆近百里之内不见匹马单人。蒙古大军凭空失踪了!
这种情况,别说是世子李睍,就是高与嵬名二令公亦感奇怪。
“敌人莫非退兵了?”
第十天头上,嵬名令公终于忍耐不住了。
“我看未必。或许是在窥伺动静吧?试图以此来麻痹我军,然后采取偷袭之术。”
对于高令公的判断,嵬名令公深表赞同。
“看来惟有如此解释啦。不过这样也好,我们是主,敌军是客,比起耐性来我们便立于不败之地了。”
正谈论间,急骤的马蹄声忽然自南面响起,打断了两位将军的猜测。不久后,他们就看到了风尘仆仆的来者。
“西壁太师?因何至此?”
看到这位朝廷大老突然出现在自己的面前,二将立时面现惊疑之色。
“二位还在此安坐吗?蒙古人已经快打到兴庆府啦!”
这位四十余岁的中年文官气急败坏的大声叫道。黄豆粒大的汗珠从他的额头上涔涔而落,焦虑惶急之色溢于言表。
“蒙古人难道是肋插双翅飞过去的吗?”
嵬名令公惊呼道。即使是对于一位沙常恨将而言,这个消息也太过惊人了。
“现在不是讨论此事的时候,还是回救都城要紧!”
西壁太师急道。做为求救使者,他现在唯一关心的就是自己的使命。
“不对!此乃围魏救赵之计!”
始终未发一言的高令公突然说道。
“不错!是有这种可能#蝴们想趁我军回援之际,半途伏击!”
一旦被提醒,嵬名令公也醒悟了过来。
“你们要抗旨吗?”
然而,无论怎样的精妙判断,在西壁太师从怀中掏出的圣旨面前,都无所施展。二将不得已做出一个折中决定。由世子李睍和高令公率一部分精兵驰援兴庆府,嵬名令公则率余众驻守原地,双方互为呼应,一旦援兵遇袭,立即自后出击,里应外合,击破蒙古军。
按照临时改变的计划,数万西夏精锐骑兵跟随着高令公出发了。他们一路急行军,同时不断派出斥候与斡罗孩城保持联系。在西壁太师的不断催促下,这支部队于三日三夜之内不眠不休地狂奔五百里,直至距兴庆不足百里之处也未遇到蒙古军的一兵一卒。
“难道是我精神过敏了吗?”
看着身边催马疾驰于清晨朝阳之中的世子李睍,高令公的心中一阵困惑。然而无论如何,眼前的状况绝非自己所乐见。原本是以逸待劳的部队不得不疲于奔命,完全是处于被敌人调动起来的不利境地。而敌人呢?直到目前为止,尚未见其影踪。
——这分明是在与幽灵作战嘛。
诸如此类的抱怨,已经开始在疲惫的士兵之中悄然传播起来。军心已经浮动,即使真正开战,只怕也难获胜算。
“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奔走百里而趋利者,必蹶上将军。”
就在这种不祥的预感袭上心头之际,一阵骚动已经从队伍的最前方传来。
“是蒙古人!”
“仅仅是截击吗?”
这个念头刚刚闪出高令公的头脑,背后的杀声已经做出了否定的回答。随即,左右便不断有箭簇破风之声传来,彻底打破了他心中残存的侥幸之心。猝不及防的西夏军在突然袭击面前,队伍立刻呈现出龟裂的态势。他们很想组织起有效的反击,但是近乎枯竭的体力和毫无准备的精神都不足以支持这种想法。何况蒙古军并不主动接近他们,只是不断的在远处游击骑射,以无情的冷箭不断侵削着他们的阵形,吞噬他们的生命。
“结成圆阵,就地防御!”
高令公扯开嗓子大叫道。他希望自己的部下能够按照事先的计划尽快恢复镇静,采取守势,等候嵬名令公的援军。然而,他的计划之中却并未将急行军的疲劳计算进来。手握圣旨的西壁太师完全破坏了整个的构想。眼见军队溃不成军,高令公心中大悔,暗恨自己过于软弱,竟不能与之据理力争。
“保护世子,准备突围!”
一路上越俎代庖的西壁太师又一次干扰军机,发布了一道对此时此地来说最为愚蠢的命令。在他的心目之中,这些士兵都是无阻轻重的棋子,为了保护上位者而可以随时丢弃的壁虎尾巴。
“不可!世子若逃,全军不保!”
忍无可忍的高令公一把抓住李睍的马缰绳,大声阻止道。
“世子若不保,你们性命难保!”
西壁太师的回答亦同样不容商量。两道目光彼此僵持着,被夹在其中的世子李睍左顾右盼,讷讷地欲言又止。显然,他也在自己与全军的安危之间难以决断。
“唉,不及其父多矣。”
一旦想到那位素以刚毅果决而令人心折的皇帝李安全,高令公的心中复觉无奈。论才具气魄,这位皇帝确实是近几代西夏之主中出类拔萃的人物,其言谈举止大有开国皇帝李元昊的神韵。当他向世子宣布严禁干涉将领权限的旨意时,自己心中的第一感触就是想大喊一声“我主英明”!然而,打破这个禁令的人,却偏偏是他自己。何谓无可奈何,惟此惟是了。
颓然之意一起,高令公顿感全身无力,马缰自他的手指之间松脱开来。西壁太师见状,立即招呼手下的侍从簇拥着世子夺路而走。催马驰出几步,他转身问道:
“你不来吗?”
高令公凄然一笑道:
“身为一军之主,岂能弃军而逃?我来断后掩护你们吧。”
“但愿你能平安无事,我在兴庆府等你!”
留下这句话后,西壁太师的身影就尾随着世子消失于乱军从中。目送他们远去后,高令公立刻下令全军向反方向突围。在他想来,即使全军溃败,也至少要设法与斡罗孩城尽量靠近,以期尽快获得嵬名令公的助力。在他的思维之中,依旧没有放弃最初的那个里应外合的计划。然而,他却不知,西夏军的行动正是蒙古军发动总攻的信号。包围圈开始缩小,巨大的网罗逐渐收拢起来!
冲在最前面的军队迎面遭遇了较之适才远为密集的箭簇攻击,立时倒下了一片。后面跟进的人吃了一惊,发声喊后,本能地向后退却。可是后面跟进的人对此全然不知,继续前涌,双方互相碰撞,立刻引发了一场大混乱。乘此时机,四外的蒙古骑兵立即呼啸而至,不但继续放箭,还有更加锋利的标枪也不断投射过来,将本已慌乱无措的西夏军打得晕头转向,无力还击。
见此情景,高令公暗叫一声“不好”,连忙带领身边的亲兵冲上去弹压局面,试图重整队伍。可是,他立刻发现自己的想法过于天真了。同样的混乱在背后和左右相继发生,使得他既便是有心,却也无力做为。他发现,这些蒙古伏兵并非直接发动攻击,而是以小股部队的姿态一波又一波地接近,到达一定距离后便不向前,而是策马横行跑动,将箭簇不断射入自军从中,无论是否射中,却绝不做片刻留顾,稍加接触即飘然远飏。他们的行动迅捷无比,所施展的打击如同不断敲击下来的锤凿般,干脆有力,将自己的部队敲击得千疮百孔,遍体鳞伤。
面对这种超乎常识之外的战法,饶是高令公老于行伍却也一时无计可施。现在,他只知道一点,无法击破对方的自己只能坐以待毙,任凭对方一口一口将自军吃掉。将近晌午的时候,随着人数的不断锐减,西夏军被压缩成了一团乱麻。直到此时,蒙古军才真正发动了短兵相接的攻击。数支部队化作锋锐的刀剑,切割着西夏人的生命,一层又一层的士兵哀号着倒下,在这种抽丝剥茧的攻势下化作铁蹄下的血泥肉屑。
高令公狠狠地咬着牙关,催马上前迎击。当此情境之下,他对自己的命运已经有所觉悟,希望以自己的死来终结这种令他窒息的折磨。不久后,他就遭遇了蒙古的一位大将。对方的点钢蛇矛挂动慑人的寒风,疾刺向他的心窝。
“当啷”一声,高令公挥刀格开,反手横斩向前,希冀在战死之前至少能够斩杀一个有些身份的敌将。可惜,他立刻发现对方绝非易与之辈,武艺之高超远在自己的想象之上。数招之间,反而被对方的反击所牵制,丧失了主动。又复数合,刀势为长枪所破,直接荡出了外门,胸腹一带门户大开,冰冷的寒风直透肌肤。
“到此为止啦!”
高令公双眼一阖,放弃了抵抗。随即,他感到身体被一阵大力所掀动,身子不由自主得倾斜着翻倒下去,怦然落地。及至他清醒过来的时候,已经被扑过来的蒙古军所擒获,牢固地捆绑了起来。
“你是谁?”
仰望着击败自己的敌手,高令公沉声问道。
“我乃蒙古成吉思大可汗部下速不台是也!看你也算一条好汉,这才说与你知。记住这个名字吧!”
那人冷冷地回答过后,继续纵马向前冲杀而去。
※※※ ※※※ ※※※
主将的被俘,彻底瓦解了西夏军最后的抵抗力量,不断有士兵弃械降伏,数万大军仅仅一个上午即宣告全军覆没。
数日后,身为俘虏的高令公在蒙古大营中见到了自己的同僚嵬名令公,这才得知斡罗孩城的最终命运。蒙古军利用降军赚开了城门,措手不及的嵬名令公被蜂拥而入的蒙古军一举活捉。随即,两位不幸的将军又遇到了另一个熟人——西壁太师。身负掩护世子的他这次终于没有放弃职责,宁可只身断后,也没让李睍落入蒙古军的手中。他虽然是一名文官,却也修习过几年武艺,马上争战的本领也着实有那么一点,可惜他遇到的对手是蒙古骁将之中的骁将忽必来。做为军务长官的他依旧不习惯只是阵头指挥的职务,因此在分派军令之后就把自己的权限交予身边的木华黎来代管,然后披坚执锐,奋武扬威地杀入敌群之中。他只是发现这一小队唐兀人形状可疑,却无巧不巧地截住了敌国的世子和重臣。西壁太师岂是他的敌手,三招两式后就被走马活擒。只是在这短暂的片刻迟延,却使得另一条更大的鱼从他的指缝间滑脱。事后,忽必来连呼后悔,却也只能徒呼奈何了。
听说世子脱险,两位战败的将军这才轻轻地舒了一口气。心想:这个人的忠诚之心虽然盲目了一些,倒也并非全无好处。
抓获他们的蒙古军似乎并不急于处决他们,只是严密看守,不令三人有逃跑的机会。其实,既便此时要对其加以释放,三人也感觉没有脸面再踏入兴庆府的城门。然而,对于他们的感受,蒙古军根本无从察知,还是带着三个俘虏不断逼进兴庆府。
突入河套之后,蒙古军迅速对兴庆府展开合围。丧失机动兵力的唐兀人只得放弃郊区,退守城市,凭依其典型的中国式要塞(4)的坚固城防来对抗。果然,在这由土木工程所建造的人为防线面前,野战无敌的骑兵军团因缺乏必要的工兵和攻坚器械而显得一筹莫展,此前诈取斡罗孩城的计策也是可一而不可二。对此,成吉思汗却并不急于求成。他下令除了留下部分军队继续监视兴庆府外,余者兵分三路,由者别、速不台和木华黎分别统领,发动了周边地区的扫荡,掠取了大量的百姓和财富,同时切断了兴庆府与河西走廊的联络,使之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之中。然而,这座坚固的城市还是岿然不动。
在一对峙局面,一直保持到了纪元1209年的夏初时节。在这段时期内,成吉思汗悠然地率领大军在贺兰山一带游动,见识了传闻中如飞腾的苍龙般起伏跌宕于高山峡谷之间的万里长城和奔流不绝的黄河。这条大河从城西流过,在城南猛然掉头,如同迷路的孩子般在城东逡巡徘徊着,最终还是找到了自己的归路,发出恍然大悟般的轰然涛声,一路前冲而去,消失于视线的末尾。
“好宽的幅面啊!恐怕将斡难、克鲁涟与土兀剌三条河并列起来,也不如它宽阔呢。”
身边传来忽必来的声音,打断了成吉思汗的思绪。一旦脱离冥想后,他的头脑立刻回到了现实之中。他反复琢磨着这句话,忽而低头俯视湍急的河水,忽而抬首遥望坚固的城墙,一个大胆的计划在他的心中逐渐现出了端倪。
翌日,成吉思汗交给忽必来一个任务——凿开河堤,引水灌城。忽必来不折不扣地执行了这个命令,经过众多士兵日以继夜的努力,用巨石修葺的河堤被掘开了数个豁口,水浪立刻咆哮着冲出河床,灌入田野。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河水并未按照预期的目的涌向兴庆府,而是沿着地势的高低幅度向位于低洼开阔地上的蒙古军营杀来。原来,缺乏必要的土木工程知识的蒙古人在破坏河堤的时候搞错了位置,使得自身反受其殃。幸而成吉思汗果断地下令立即移营,才避免了全军被洪水淹没的厄运。饶是如此,还是有百余人和大批做为军粮的羊群葬身水府。这常寒攻计划亦以失败的结局而告终。
做为主管者,忽必来向成吉思汗请求处分。成吉思汗一笑而罢,劝慰道:
“命令是我亲自下达的,责任在我,与你无关。是我将事情想得过于简单,才酿成了这场祸事。不过,这也并不完全是坏事,至少使我们积累了经验,避免以后重蹈覆辙。”
话虽如此,可是这一损失无疑是巨大的,其直接后果几乎导致对唐兀的征伐无以为继。不过,这次行动对于城内的人们也起到了一定的威吓效果。假如蒙古人下次吸取教训,再次发动这种水攻战术,那么受害者必定就是自己了。何况,蒙古军在其国土上的横冲直撞,也严重影响了唐兀惕的国计民生。与所有建立于丝绸之路上的国家别无二致,唐兀惕人所依赖的商路因战争而关闭,许多以经商为生的百姓的生活水准直线下降,导致民心厌战,士气低糜。迫于形式,李安全派出使者,向蒙古乞和。
成吉思汗眼见急切间也不能完全征服敌手,便明智地接受了这个建议。纪元1209年秋初,唐兀惕正式向蒙古降伏,此后将以藩属的身份尊奉蒙古的号令。同时,献上了大量的贡品,其中包括本地特产的漂亮的白骆驼和一名据说是李安全的亲生女儿的公主(5)。做为交换,成吉思汗命令释放了三位被俘的唐兀重臣——两位令公和一位太师。三人如何满面羞惭地返回兴庆府,又将受到如何的惩罚,略过不提。
从唐兀惕回师的时候,成吉思汗没有直接北返蒙古,而是挥军向东,沿万里长城逶迤而行,突然出现在汪古惕部的领地之上。原来,在他进攻唐兀惕的时候,一个不幸的噩耗传来,自杭爱山战胜乃蛮以来,始终以忠实的盟友与属臣的身份拥护蒙古的阿剌忽失特勤汗被部落中那些亲金国贵族们所谋害。成吉思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平灭了汪古惕人的叛乱,重新将阿剌忽失特勤汗的儿子赤古扶上了汗位,杀掉了一批作乱贵族首领,建立了一个亲蒙古的政权,确保了未来攻击金国的前哨阵地的稳定与进军途径的畅通。
从纪元1207年到1209年,成吉思汗的蒙古大军,向北燃烧了泰加森林,向西翻越了阿勒台山,向南横跨了大沙漠,完成了对周边新月形地区的征服与平定,将一个统一、强大、稳定的蒙古帝国逐步巩固了起来,并巍然屹立于北亚高原之上。当这个新月变成满月的时候,无数的苍狼势必以风林火山之姿,纵横驰骋之态,在世界的舞台上掀起滔天巨浪,淹没那些躺在自身古老悠久文明之上犹自昏昏欲睡的民族与国家。
——听!蒙古马在嘶鸣,弓弦在嗡嗡震颤,渴望饮血的宝刀在鞘内胡胡作响!复仇的序曲如此雄浑!——
(1)《拉施特书》则说:成吉思汗进军额里孩城,这个地名令我们想到了《马可.波罗游记》里所提到的对宁夏的称呼——额格里合牙。
(2)斡罗孩,音Wo-lo-hai。
(3)李安全,国史称襄宗,亦可作“赵安全、拓拔安全”(关于西夏帝王的姓氏,大约是曾经建立于中国版图上的各个国家中最为复杂的。在这三个姓氏之中,以其党项固有之“拓拔”姓氏最为久远,赵姓则是来自宋朝的赐予。当党项立国后便摒弃了此姓,同时为了赢得当地汉族的支持,恢复了唐朝所赐予的李姓,做为其国姓)。纪元1206—1211年在位。《拉施特书》称之为失都儿忽(Chidhou),在吐蕃语作Srong-btsan,意为“公正”、“正直”、“诚实”。然校《秘史》与《元史》勘之,实误,应为末代南平王李睍(1226-1227在位)。
(4)《秘史》称:唐兀惕是“一个有坚固和筑城而居的城市的国家”(nduguksen baqasou)。
(5)《萨囊彻辰书》称这位唐兀惕可贺敦的蒙古语名字为古尔伯勒津郭斡。称其是一位“面色光莹,夜不须烛”的绝代佳人。
至于风平沙静的时候,灰白色的炽烈阳光立刻将熊熊大火不断投向地面。不久后,戈壁就会变成一块变灼得通红的铁板一般变为赭石色。在这个时候,如果有谁敢于跳下骆驼背来,他的双脚立刻就会了解什么叫烧烤。高温压榨出地表上的每一丝水分,使之化为不绝的雾气,与几欲熔化的空气杂糅一处,不时在半空中发生着不规则地波动,干扰着人们的视线,使之变得扭曲变形,颠倒倒错。只有在清晨时分,才是一天中最为清爽明朗的时刻:天空挣脱出厚重夜幕的掌控,逐渐向靓丽的浅蓝色过度。不久后,晨曦的光剑刺透轻薄的雾霭,还光明于大地。那一刻,空气如山间溪流般透澈,轻快地流动于人们的鼻息肺腑之间,那感觉如丝帛般柔滑动人。视线如此悠远,可以无远弗界地延展向呈现出本色的天地尽头,近而使人辄生错觉:沿着这条路可以一直走到天上去。
成吉思汗选择的出兵时间是一年中穿越戈壁的最佳时机。来自西南方向的干燥季风未至,沿着骆驼商队所开辟的通道行进,可以不时在一些沙丘或风化严重的岩石背后附近寻到一些零星的草场,还有向地下挖掘不及两、三米甚至数呎便可涌出的清泉。有了这些休憩之地,蒙古兵马就绝偶无水草匮乏之虞。
在这里,偶而现出几间帐篷和数匹驼马的影子也算不得一件稀罕事。成吉思汗便多次亲眼看到过一些人影的晃动。这些为追逐利益而跋涉于生命边缘的人们从外表穿着上几乎全无二致。同样宽大的遮阳笠,袍子和靴子乃至稳健的步履,使他们个个都具备了孪生兄弟的特征,红褐色的砂地上驻留着他们长长的影子。这沙丘、岩石、牲畜、人形在红褐色的背景映衬下,表现极为生动。
一千多年来,每一年的这个季节和这条路,对于南方的农耕民族来说,都是相当危险的时期。成群结队的游牧民族长驱直入,出现在这条名为“河西走廊”的狭长地峡一带。再向东,是绿意盈盈的河套地区,日夜奔流的黄河在大地上划出一个大大的“几”字,将河套平原同河套以外的沙化草原一劈两半。穿越最后沙丘与盐池后,眼前的情景就因河流的走向而变得截然不同起来。
从中国古人留下的“黄河百害,唯利一套”的说法来看,这条中国北方最大的河流在此处还显得相当可爱,平静而温和地灌溉出许多草原和良田。因之而诞生的绿洲农业的富庶景象——绿树成荫、繁花似锦、果实累累、麦浪翻滚,对于刚刚走出荒凉戈壁的游牧骑兵来说,当真是如诗如画的仙境,富足安康的天国。从而激发了他们大肆掠略的热情,冷酷的铁蹄如入无人之境,困扰着历代中原统治者的心绪。
如今,这一困扰将由唐兀惕人来率先承接,而他们所面对的偏偏是千年以来各蛮族中最伟大的首领和最强悍的部队,这使得其宿命悲剧的色彩愈发浓厚起来。
唐兀惕帝国的首都名叫兴庆府(1),位于黄河大“几”字型的一撇之上,西傍贺兰山脉,东接鄂尔多斯草原,是一座典型的绿洲城市。经过二百年来的不断完善与开凿,在其郊区形成了四通八达的灌溉渠网,促进了这里发达的农业与良好的气候。同时,这也是一座属于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工商业城市。这一点,通过马可.波罗在其著名游记中所提及的大规模驼绒织品工场和同样巨大的交易量上即可窥见其当年之风采。
对唐兀惕人的征伐以斡罗孩城(2)之战揭开了序幕。负责驻守此城的唐兀惕人将军史称嵬名令公,是他率先发现了蒙古人的异常动向并立即将自己的判断上报于当时的唐兀惕王李安全。嵬名令公在奏章中指出:此次来袭的蛮族图谋甚大,绝非一般性质的劫掠,宜早图对策。
这位李安全(3),在中国历书中被称为襄宗,是于去年通过篡位的方式刚刚登上宝座的新君。按照他的年号为“应天”。因此,纪元1207年便是西夏的应天二年。从多方史书来看,李安全都不能算是一位昏君,而且相当有军事才能,即位之初也力图重振西夏之国威。在得到嵬名令公的奏章后,他立即命自己的世子李睍为主帅,以宿将高令公为副手,发重兵迎击。
他们在斡罗孩城与嵬名令公的边防部队会师后,双方迅速议定了战法。决定依托城防布阵,诱蒙古军主力前来决战。如果战胜,自不消说。若一旦不利,也可依托坚城,形成持久局面。根据游牧民族的特性,这种持久战是对方最难适应的,最终可导致对方耐性全失,不得不撤兵。届时,自后追击,可一举反败为胜。就其本质而言,这不失为一种攻守兼备、稳健合理的战法,唐兀人本身便是游牧民族的后裔,只有他们才能想到如此具有针对性的策略。这一切的计划都构架于斡罗孩城控河套要冲的险要位置之上,无论任何来自北方的入侵,都必须通过此地才能进一步染指南方的绿洲,除非敌军愿意横渡东面的黄河或不惜穿越西边的巴丹吉林沙漠。
“世子请安居城内,看末将与嵬名令公破敌。”
在高令公以此言做为整个军议的结语后,李睍点头承知。战场对于这个仅有十余岁的少年而言,确实是一件难以理解的事情。做为提升士气的标志,他能亲临前线已经完成了主要的使命。其父李安全在临出兵前已经对其职权做出了严格的规定:不得绕过前线将领发布任何指令,避免干扰将军们的战场指挥。从李安全的本心出发,他很希望自己亲自出阵,然而他必须留在都城内应付那些对自己的权威尚存异议的亲戚和臣子们。可见,篡位者的日子并不好过。
西夏军按照预定的战法在斡罗孩城下严阵以待,然而一连数日,却连蒙古人的影子都未发觉。根据远近斥候传来的消息,方圆近百里之内不见匹马单人。蒙古大军凭空失踪了!
这种情况,别说是世子李睍,就是高与嵬名二令公亦感奇怪。
“敌人莫非退兵了?”
第十天头上,嵬名令公终于忍耐不住了。
“我看未必。或许是在窥伺动静吧?试图以此来麻痹我军,然后采取偷袭之术。”
对于高令公的判断,嵬名令公深表赞同。
“看来惟有如此解释啦。不过这样也好,我们是主,敌军是客,比起耐性来我们便立于不败之地了。”
正谈论间,急骤的马蹄声忽然自南面响起,打断了两位将军的猜测。不久后,他们就看到了风尘仆仆的来者。
“西壁太师?因何至此?”
看到这位朝廷大老突然出现在自己的面前,二将立时面现惊疑之色。
“二位还在此安坐吗?蒙古人已经快打到兴庆府啦!”
这位四十余岁的中年文官气急败坏的大声叫道。黄豆粒大的汗珠从他的额头上涔涔而落,焦虑惶急之色溢于言表。
“蒙古人难道是肋插双翅飞过去的吗?”
嵬名令公惊呼道。即使是对于一位沙常恨将而言,这个消息也太过惊人了。
“现在不是讨论此事的时候,还是回救都城要紧!”
西壁太师急道。做为求救使者,他现在唯一关心的就是自己的使命。
“不对!此乃围魏救赵之计!”
始终未发一言的高令公突然说道。
“不错!是有这种可能#蝴们想趁我军回援之际,半途伏击!”
一旦被提醒,嵬名令公也醒悟了过来。
“你们要抗旨吗?”
然而,无论怎样的精妙判断,在西壁太师从怀中掏出的圣旨面前,都无所施展。二将不得已做出一个折中决定。由世子李睍和高令公率一部分精兵驰援兴庆府,嵬名令公则率余众驻守原地,双方互为呼应,一旦援兵遇袭,立即自后出击,里应外合,击破蒙古军。
按照临时改变的计划,数万西夏精锐骑兵跟随着高令公出发了。他们一路急行军,同时不断派出斥候与斡罗孩城保持联系。在西壁太师的不断催促下,这支部队于三日三夜之内不眠不休地狂奔五百里,直至距兴庆不足百里之处也未遇到蒙古军的一兵一卒。
“难道是我精神过敏了吗?”
看着身边催马疾驰于清晨朝阳之中的世子李睍,高令公的心中一阵困惑。然而无论如何,眼前的状况绝非自己所乐见。原本是以逸待劳的部队不得不疲于奔命,完全是处于被敌人调动起来的不利境地。而敌人呢?直到目前为止,尚未见其影踪。
——这分明是在与幽灵作战嘛。
诸如此类的抱怨,已经开始在疲惫的士兵之中悄然传播起来。军心已经浮动,即使真正开战,只怕也难获胜算。
“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奔走百里而趋利者,必蹶上将军。”
就在这种不祥的预感袭上心头之际,一阵骚动已经从队伍的最前方传来。
“是蒙古人!”
“仅仅是截击吗?”
这个念头刚刚闪出高令公的头脑,背后的杀声已经做出了否定的回答。随即,左右便不断有箭簇破风之声传来,彻底打破了他心中残存的侥幸之心。猝不及防的西夏军在突然袭击面前,队伍立刻呈现出龟裂的态势。他们很想组织起有效的反击,但是近乎枯竭的体力和毫无准备的精神都不足以支持这种想法。何况蒙古军并不主动接近他们,只是不断的在远处游击骑射,以无情的冷箭不断侵削着他们的阵形,吞噬他们的生命。
“结成圆阵,就地防御!”
高令公扯开嗓子大叫道。他希望自己的部下能够按照事先的计划尽快恢复镇静,采取守势,等候嵬名令公的援军。然而,他的计划之中却并未将急行军的疲劳计算进来。手握圣旨的西壁太师完全破坏了整个的构想。眼见军队溃不成军,高令公心中大悔,暗恨自己过于软弱,竟不能与之据理力争。
“保护世子,准备突围!”
一路上越俎代庖的西壁太师又一次干扰军机,发布了一道对此时此地来说最为愚蠢的命令。在他的心目之中,这些士兵都是无阻轻重的棋子,为了保护上位者而可以随时丢弃的壁虎尾巴。
“不可!世子若逃,全军不保!”
忍无可忍的高令公一把抓住李睍的马缰绳,大声阻止道。
“世子若不保,你们性命难保!”
西壁太师的回答亦同样不容商量。两道目光彼此僵持着,被夹在其中的世子李睍左顾右盼,讷讷地欲言又止。显然,他也在自己与全军的安危之间难以决断。
“唉,不及其父多矣。”
一旦想到那位素以刚毅果决而令人心折的皇帝李安全,高令公的心中复觉无奈。论才具气魄,这位皇帝确实是近几代西夏之主中出类拔萃的人物,其言谈举止大有开国皇帝李元昊的神韵。当他向世子宣布严禁干涉将领权限的旨意时,自己心中的第一感触就是想大喊一声“我主英明”!然而,打破这个禁令的人,却偏偏是他自己。何谓无可奈何,惟此惟是了。
颓然之意一起,高令公顿感全身无力,马缰自他的手指之间松脱开来。西壁太师见状,立即招呼手下的侍从簇拥着世子夺路而走。催马驰出几步,他转身问道:
“你不来吗?”
高令公凄然一笑道:
“身为一军之主,岂能弃军而逃?我来断后掩护你们吧。”
“但愿你能平安无事,我在兴庆府等你!”
留下这句话后,西壁太师的身影就尾随着世子消失于乱军从中。目送他们远去后,高令公立刻下令全军向反方向突围。在他想来,即使全军溃败,也至少要设法与斡罗孩城尽量靠近,以期尽快获得嵬名令公的助力。在他的思维之中,依旧没有放弃最初的那个里应外合的计划。然而,他却不知,西夏军的行动正是蒙古军发动总攻的信号。包围圈开始缩小,巨大的网罗逐渐收拢起来!
冲在最前面的军队迎面遭遇了较之适才远为密集的箭簇攻击,立时倒下了一片。后面跟进的人吃了一惊,发声喊后,本能地向后退却。可是后面跟进的人对此全然不知,继续前涌,双方互相碰撞,立刻引发了一场大混乱。乘此时机,四外的蒙古骑兵立即呼啸而至,不但继续放箭,还有更加锋利的标枪也不断投射过来,将本已慌乱无措的西夏军打得晕头转向,无力还击。
见此情景,高令公暗叫一声“不好”,连忙带领身边的亲兵冲上去弹压局面,试图重整队伍。可是,他立刻发现自己的想法过于天真了。同样的混乱在背后和左右相继发生,使得他既便是有心,却也无力做为。他发现,这些蒙古伏兵并非直接发动攻击,而是以小股部队的姿态一波又一波地接近,到达一定距离后便不向前,而是策马横行跑动,将箭簇不断射入自军从中,无论是否射中,却绝不做片刻留顾,稍加接触即飘然远飏。他们的行动迅捷无比,所施展的打击如同不断敲击下来的锤凿般,干脆有力,将自己的部队敲击得千疮百孔,遍体鳞伤。
面对这种超乎常识之外的战法,饶是高令公老于行伍却也一时无计可施。现在,他只知道一点,无法击破对方的自己只能坐以待毙,任凭对方一口一口将自军吃掉。将近晌午的时候,随着人数的不断锐减,西夏军被压缩成了一团乱麻。直到此时,蒙古军才真正发动了短兵相接的攻击。数支部队化作锋锐的刀剑,切割着西夏人的生命,一层又一层的士兵哀号着倒下,在这种抽丝剥茧的攻势下化作铁蹄下的血泥肉屑。
高令公狠狠地咬着牙关,催马上前迎击。当此情境之下,他对自己的命运已经有所觉悟,希望以自己的死来终结这种令他窒息的折磨。不久后,他就遭遇了蒙古的一位大将。对方的点钢蛇矛挂动慑人的寒风,疾刺向他的心窝。
“当啷”一声,高令公挥刀格开,反手横斩向前,希冀在战死之前至少能够斩杀一个有些身份的敌将。可惜,他立刻发现对方绝非易与之辈,武艺之高超远在自己的想象之上。数招之间,反而被对方的反击所牵制,丧失了主动。又复数合,刀势为长枪所破,直接荡出了外门,胸腹一带门户大开,冰冷的寒风直透肌肤。
“到此为止啦!”
高令公双眼一阖,放弃了抵抗。随即,他感到身体被一阵大力所掀动,身子不由自主得倾斜着翻倒下去,怦然落地。及至他清醒过来的时候,已经被扑过来的蒙古军所擒获,牢固地捆绑了起来。
“你是谁?”
仰望着击败自己的敌手,高令公沉声问道。
“我乃蒙古成吉思大可汗部下速不台是也!看你也算一条好汉,这才说与你知。记住这个名字吧!”
那人冷冷地回答过后,继续纵马向前冲杀而去。
※※※ ※※※ ※※※
主将的被俘,彻底瓦解了西夏军最后的抵抗力量,不断有士兵弃械降伏,数万大军仅仅一个上午即宣告全军覆没。
数日后,身为俘虏的高令公在蒙古大营中见到了自己的同僚嵬名令公,这才得知斡罗孩城的最终命运。蒙古军利用降军赚开了城门,措手不及的嵬名令公被蜂拥而入的蒙古军一举活捉。随即,两位不幸的将军又遇到了另一个熟人——西壁太师。身负掩护世子的他这次终于没有放弃职责,宁可只身断后,也没让李睍落入蒙古军的手中。他虽然是一名文官,却也修习过几年武艺,马上争战的本领也着实有那么一点,可惜他遇到的对手是蒙古骁将之中的骁将忽必来。做为军务长官的他依旧不习惯只是阵头指挥的职务,因此在分派军令之后就把自己的权限交予身边的木华黎来代管,然后披坚执锐,奋武扬威地杀入敌群之中。他只是发现这一小队唐兀人形状可疑,却无巧不巧地截住了敌国的世子和重臣。西壁太师岂是他的敌手,三招两式后就被走马活擒。只是在这短暂的片刻迟延,却使得另一条更大的鱼从他的指缝间滑脱。事后,忽必来连呼后悔,却也只能徒呼奈何了。
听说世子脱险,两位战败的将军这才轻轻地舒了一口气。心想:这个人的忠诚之心虽然盲目了一些,倒也并非全无好处。
抓获他们的蒙古军似乎并不急于处决他们,只是严密看守,不令三人有逃跑的机会。其实,既便此时要对其加以释放,三人也感觉没有脸面再踏入兴庆府的城门。然而,对于他们的感受,蒙古军根本无从察知,还是带着三个俘虏不断逼进兴庆府。
突入河套之后,蒙古军迅速对兴庆府展开合围。丧失机动兵力的唐兀人只得放弃郊区,退守城市,凭依其典型的中国式要塞(4)的坚固城防来对抗。果然,在这由土木工程所建造的人为防线面前,野战无敌的骑兵军团因缺乏必要的工兵和攻坚器械而显得一筹莫展,此前诈取斡罗孩城的计策也是可一而不可二。对此,成吉思汗却并不急于求成。他下令除了留下部分军队继续监视兴庆府外,余者兵分三路,由者别、速不台和木华黎分别统领,发动了周边地区的扫荡,掠取了大量的百姓和财富,同时切断了兴庆府与河西走廊的联络,使之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之中。然而,这座坚固的城市还是岿然不动。
在一对峙局面,一直保持到了纪元1209年的夏初时节。在这段时期内,成吉思汗悠然地率领大军在贺兰山一带游动,见识了传闻中如飞腾的苍龙般起伏跌宕于高山峡谷之间的万里长城和奔流不绝的黄河。这条大河从城西流过,在城南猛然掉头,如同迷路的孩子般在城东逡巡徘徊着,最终还是找到了自己的归路,发出恍然大悟般的轰然涛声,一路前冲而去,消失于视线的末尾。
“好宽的幅面啊!恐怕将斡难、克鲁涟与土兀剌三条河并列起来,也不如它宽阔呢。”
身边传来忽必来的声音,打断了成吉思汗的思绪。一旦脱离冥想后,他的头脑立刻回到了现实之中。他反复琢磨着这句话,忽而低头俯视湍急的河水,忽而抬首遥望坚固的城墙,一个大胆的计划在他的心中逐渐现出了端倪。
翌日,成吉思汗交给忽必来一个任务——凿开河堤,引水灌城。忽必来不折不扣地执行了这个命令,经过众多士兵日以继夜的努力,用巨石修葺的河堤被掘开了数个豁口,水浪立刻咆哮着冲出河床,灌入田野。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河水并未按照预期的目的涌向兴庆府,而是沿着地势的高低幅度向位于低洼开阔地上的蒙古军营杀来。原来,缺乏必要的土木工程知识的蒙古人在破坏河堤的时候搞错了位置,使得自身反受其殃。幸而成吉思汗果断地下令立即移营,才避免了全军被洪水淹没的厄运。饶是如此,还是有百余人和大批做为军粮的羊群葬身水府。这常寒攻计划亦以失败的结局而告终。
做为主管者,忽必来向成吉思汗请求处分。成吉思汗一笑而罢,劝慰道:
“命令是我亲自下达的,责任在我,与你无关。是我将事情想得过于简单,才酿成了这场祸事。不过,这也并不完全是坏事,至少使我们积累了经验,避免以后重蹈覆辙。”
话虽如此,可是这一损失无疑是巨大的,其直接后果几乎导致对唐兀的征伐无以为继。不过,这次行动对于城内的人们也起到了一定的威吓效果。假如蒙古人下次吸取教训,再次发动这种水攻战术,那么受害者必定就是自己了。何况,蒙古军在其国土上的横冲直撞,也严重影响了唐兀惕的国计民生。与所有建立于丝绸之路上的国家别无二致,唐兀惕人所依赖的商路因战争而关闭,许多以经商为生的百姓的生活水准直线下降,导致民心厌战,士气低糜。迫于形式,李安全派出使者,向蒙古乞和。
成吉思汗眼见急切间也不能完全征服敌手,便明智地接受了这个建议。纪元1209年秋初,唐兀惕正式向蒙古降伏,此后将以藩属的身份尊奉蒙古的号令。同时,献上了大量的贡品,其中包括本地特产的漂亮的白骆驼和一名据说是李安全的亲生女儿的公主(5)。做为交换,成吉思汗命令释放了三位被俘的唐兀重臣——两位令公和一位太师。三人如何满面羞惭地返回兴庆府,又将受到如何的惩罚,略过不提。
从唐兀惕回师的时候,成吉思汗没有直接北返蒙古,而是挥军向东,沿万里长城逶迤而行,突然出现在汪古惕部的领地之上。原来,在他进攻唐兀惕的时候,一个不幸的噩耗传来,自杭爱山战胜乃蛮以来,始终以忠实的盟友与属臣的身份拥护蒙古的阿剌忽失特勤汗被部落中那些亲金国贵族们所谋害。成吉思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平灭了汪古惕人的叛乱,重新将阿剌忽失特勤汗的儿子赤古扶上了汗位,杀掉了一批作乱贵族首领,建立了一个亲蒙古的政权,确保了未来攻击金国的前哨阵地的稳定与进军途径的畅通。
从纪元1207年到1209年,成吉思汗的蒙古大军,向北燃烧了泰加森林,向西翻越了阿勒台山,向南横跨了大沙漠,完成了对周边新月形地区的征服与平定,将一个统一、强大、稳定的蒙古帝国逐步巩固了起来,并巍然屹立于北亚高原之上。当这个新月变成满月的时候,无数的苍狼势必以风林火山之姿,纵横驰骋之态,在世界的舞台上掀起滔天巨浪,淹没那些躺在自身古老悠久文明之上犹自昏昏欲睡的民族与国家。
——听!蒙古马在嘶鸣,弓弦在嗡嗡震颤,渴望饮血的宝刀在鞘内胡胡作响!复仇的序曲如此雄浑!——
(1)《拉施特书》则说:成吉思汗进军额里孩城,这个地名令我们想到了《马可.波罗游记》里所提到的对宁夏的称呼——额格里合牙。
(2)斡罗孩,音Wo-lo-hai。
(3)李安全,国史称襄宗,亦可作“赵安全、拓拔安全”(关于西夏帝王的姓氏,大约是曾经建立于中国版图上的各个国家中最为复杂的。在这三个姓氏之中,以其党项固有之“拓拔”姓氏最为久远,赵姓则是来自宋朝的赐予。当党项立国后便摒弃了此姓,同时为了赢得当地汉族的支持,恢复了唐朝所赐予的李姓,做为其国姓)。纪元1206—1211年在位。《拉施特书》称之为失都儿忽(Chidhou),在吐蕃语作Srong-btsan,意为“公正”、“正直”、“诚实”。然校《秘史》与《元史》勘之,实误,应为末代南平王李睍(1226-1227在位)。
(4)《秘史》称:唐兀惕是“一个有坚固和筑城而居的城市的国家”(nduguksen baqasou)。
(5)《萨囊彻辰书》称这位唐兀惕可贺敦的蒙古语名字为古尔伯勒津郭斡。称其是一位“面色光莹,夜不须烛”的绝代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