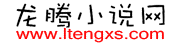4.说唱艺术
随着文化的提高,更具规范性的艺术作品亦随之应运而生,于是以韵文为主体的说唱艺术应运而生了。其分类为“赞祝词”、“诗”和“史诗”。
做为蒙古族最为古老的韵文说唱艺术的赞祝词与珊蛮教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继兴创作或牢记熟背固有作品,则成为衡量一名珊蛮巫师的能力高低的重要标准。
如果你来到十一至十三世纪的蒙古,将于各种放牧、狩猎、战争、新婴诞生、婚礼、节日以及大型饮宴娱乐活动的时候,总会看到那些载歌载舞的珊蛮巫师们的身影。做为早期蒙古人中率先掌握各种文化知识的他们,普遍受到无比的尊崇与敬畏,即使是在成吉思汗时代,他们在民众心目之中依旧保有强大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力都或多或少得与那些富于哲理,悠扬动听的赞祝词难以分开。
在蒙古人看来,能够得到珊蛮巫师吟诵祝福是无比吉祥的象征,这种传承于上古神话传说,内容欢畅,形式上首韵互和,通俗易懂,平实可亲、琅琅上口的歌词,会传达长生天神的意愿,为牧民的心灵带领安宁平和并保佑阖家人畜平安。
蒙古赞祝词的内容的取材也是十分广泛的,其中不仅包括歌颂上古神灵、人类英雄业绩、天体气候变化、山川风物沿革等等恢宏壮阔的大事,也有对自然现象、风物景色、放牧生活、野兽家畜、起居饮食、日常生活、风土人情等等细节方面的描述评说,既体现了早期神秘主义的特色,又充满了人文写实色彩,因而为广大蒙古人民所喜闻乐见。下面,将从其中选结一二,做为例证。
摔跤手赞
从七勃里(外)挥舞而来,
震得地动山摇;
从八勃里(外)挥舞而来,
踏得山川颤抖;
咆哮着狂舞而至,
越舞越有力气。
从前面猛看过去,
犹如一只斑虎;
从后面乍看过去,
牵浩一头狸虎。
他有雄狮般的力气,
他有巨象般的身躯。
这摔跤手的技巧啊,
实在令人惊奇。
(选自色道儿吉义编译《蒙古族历代文学作品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2,P52)
众所周知,摔跤、射箭与马术为蒙古族的“男人三绝”,而摔跤在其尤站胜场。通常,一名优秀的摔跤手在人们心目之中就是男子汉的典范。在古代蒙古,摔跤不仅是庆典上奉献给神灵的表演,同时也是男人之间解决彼此恩怨的一种决斗方式。比如成吉思汗就曾经命令他的弟弟别勒古台与伤害过他不里孛阔要求通过摔跤做为决斗方式,而成吉思汗的另一个幼弟帖木格则向阔阔出提出以摔跤的方式了解二人之间的恩怨。通过这些历史上著名的决斗场面,足以确定摔跤一术在蒙古人心目之中的至高地位。因此,如上这样一首歌颂摔跤手的赞祝词的出现,也绝非孤立的现象。在这首词中,那位迭名作者不惜采取夸张、比喻等等手法,用集尽溢美的赞颂之词,将一位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摔跤手步入场地之时的种种行动、表情刻划得细致入微,令读者不禁产生了身临其境的感觉。
骏马赞
它那飘飘欲舞的轻美长鬃,
好像闪闪发光的金桑烘风旋转;
它那炯炯发光的两只眼睛,
好像一对金鱼在水中游玩;
它那宽阔无比的胸膛,
好像滴满了甘露的宝壶;
它那精神抖擞的两只耳朵,
好像山顶上盛开的莲花瓣;
它那震动大地的响亮回音,
好像动听的海螺发出的吼声;
它那宽敞而舒适的鼻孔,
好像巧人编织的盘肠;
它那潇洒而秀气的尾巴,
好像色调醒目的彩绸;
它那坚硬的四只圆蹄,
好像风驰电掣的风火轮;
它全力汇聚了八宝的形状,
这神奇的骏马啊,真是举世无双。
(见前引书,P48)
蒙古族是马背上的民族,马之于人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因此,它们也是蒙古人心中最为重要的存在,因此赞颂其丰姿仪态的作品也为数甚多。做为重要的交通工具和战争资源,马的形象渗透了蒙古人的全部生活,甚至形容一个人的优秀,也往往比之于马,例如成吉思汗麾下的四位名将——博儿术、木华黎、赤老温、孛罗兀勒就有这“四骏”之美名。再看这首赞词,其中运用了大量的排比句式来描述骏马的各个部位,每一处都以另一种美好的事物来加以比喻形容,突显了骏马奔走时的健美体态和迅捷速度。而如此形象隽永的词句,则将作者对马的喜爱之情表露无遗,也正因其倾心歌颂的真情实感,使得一匹骏马的血肉灵魂尽展于读者的面前,其鲜活灵动的形象呼之欲出。
也就是在这段文化大发展的时期,通常意义上的诗创造也渐渐萌芽并迅速达到了鼎盛时期。根据波斯学者们的记述,蒙古人喜欢通过诗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内心情感和思想,采取抒情诗方式来展现个人意愿的形式已经成为了当时的一种普遍现象。这其中最具代表意义的文字类作品就是人称“天下奇书”的《蒙古秘史》(关于这部具有多方面价值的巨著的具体情况,将在专门章节之中做出介绍)。因此,也可以这样说,《秘史》本身就是一部纪元十二至十三世纪的蒙古诗歌总集。据统计,全书共收录诗作122首,而就其通常分段来看,228段的文字之中几乎每两段就有一首诗作,其出现频率之高亦无愧于诗集之称。
书中的诗歌,风格多样,内容广泛,可分为:叙人、记事、外交词令、讽刺小品、赞歌、哲理训诫、誓词、规劝词等等形式。其作者上迄成吉思汗,下至无名的草原诗人,可谓函概了当时蒙古社会的各个层面。这些诗句,或雄浑激扬,或苍凉古朴,或情深意切,或风趣幽默,遣词别致,意境深刻,行文流畅,修辞考究,表现了一个民族在其上升期内所表现出来的智慧与自信。
做为一个民族的历史与未来的代表,史诗在文学与历史上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蒙古族的史诗同样具有丰富的文化底蕴和身后的历史积淀。200年来,世界各国的学者们无不为其着迷,经过悉心搜集和整理,现在已知的蒙古族史诗数量竟然高达300余首(剔除其中变体部分,亦不下80部),其数量之多,在世界各民族文学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如此卷帙浩繁的史诗,既是研究蒙古历史的不可多得的第一手材料,也为古代世界文学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也是蒙古族文化的骄傲。
在众多史诗之中,以英雄史诗类型的作品为最,民间通常称其为“镇压蟒古斯的故事”。根据其篇幅,学者将其分类为“单本史诗”和“长篇传记史诗”。就其生成年代,目前学界尚无准确的定论,只是将其大体的时间范围圈定为奴隶社会阶段,这种结论完全源自那个时期全世界普遍的英雄崇拜思想的共性而言,其繁荣阶段应不晚于《蒙古秘史》,主要的传播载体依旧保留于说唱艺人的口头。当然,这其中很多作品本身就属于民间口头创作。
所谓蟒古斯,是蒙古神话之中最大的恶魔,它有着无数个凶恶丑陋的头颅,代表世间一切黑暗、丑恶、愚昧与罪行,凝聚了无比强大的邪恶之力,是一切善良、正义与美好事务的对立面。然而,在蒙古人的心目之中,与之发生对决的却不是神灵,而是来自人类之中的英雄。可见,此时的蒙古人已经通过与严酷自然的搏斗,人文意识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从而摆脱了蒙昧期的惟神论的影响,转而崇敬起来自同类之中的优秀人物。来自人群之中的“把阿秃儿”们成为了赞颂的主体,他们高举神奇的武器,骑乘神骏的良驹,发挥自身的高超技艺和绝顶智慧,一次又一次地击败了来自恶魔“蟒古斯”的侵袭,保护了自己的人民,从而赢得了无限的敬仰,也就此成为作品之中被加以浓墨重彩描述的核心人物。
这些英雄不仅精通“男子三绝”,更具备诸如忠诚、勇猛、善良,正直等等一切人类最高的美德,同时,他们也会在对抗邪恶的征途中遇到各种各样的人物,还会因此与美丽温柔的牧羊女发生纯洁真挚的爱情。人性化的描写使得他们摆脱了神格,而化作一个又一个有血有肉、形象丰满、可敬可亲的形象。他们的胜利,往往并非一人之力,总是得到各种力量的协助,显得真实生动,同时也反映了当时的人们在自然压力之下的不屈精神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诚然,这些英雄也有着与众不同的出身和超越常识的本领:他们吃饭的时候用七十人才能抬动的大碗,可以举起牛犊大小的巨石去击打敌人,坐骑的鞍子放在地面上就像一座小山。他们因为自身力量的强大,因而产生了无比的自信。他们认为自己的身体是“父母给予的”,与任何神的恩赐无关,于是他们屡次击败恶魔“蟒古斯”的功绩也只能属于自己,而并非天意相助。他们摆脱了对天的敬畏,甚至公然发出挑战苍天的声音,为了“与腾格里神战斗而生”(《汗哈仍贵》)#蝴们敢于蔑视神权,挑战巫师(《古诺干勇士》),甚至为了保卫自己的爱人而与神发生殊死搏斗,并取得最终的胜利(《青格勒汗》)。由此可见,史诗的出现标志着神权思想的解体,直到十七世纪黄教传入前,蒙古人的思想领域之中充满了浪漫主义和人文主义的思想。
史诗的表现手法相当自由,而去相当注意情节之上的起承转合,具有相当精强的故事性与可读性。它的写作往往围绕着一个中心来展开情节,又于其中穿插了一些与之相关的其它小故事,当高氵朝情节即将来临之前,又很巧妙的安排下一些小高氵朝,以大海升波之势层层递进,步步铺垫,将整个故事自然而然的推上了华彩颠峰。使听众于满足娱乐感观之余,又感合情合理,毫无突兀之感。同时,说唱者通过自己的语言功力和音乐衬托,将听众带入到故事情节之中,身临其境之感油然而生。
做为民间艺术的典型代表,史诗摆脱了韵文体诗歌的拘束,还原了蒙古人最初的自由文学题材,摒弃了渲染神秘主义的晦涩语句和呆板格式,以通俗生动的语言和灵活多变的风格浸入人类生活之中的各个思想领域,为蒙古语言文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随着文化的提高,更具规范性的艺术作品亦随之应运而生,于是以韵文为主体的说唱艺术应运而生了。其分类为“赞祝词”、“诗”和“史诗”。
做为蒙古族最为古老的韵文说唱艺术的赞祝词与珊蛮教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继兴创作或牢记熟背固有作品,则成为衡量一名珊蛮巫师的能力高低的重要标准。
如果你来到十一至十三世纪的蒙古,将于各种放牧、狩猎、战争、新婴诞生、婚礼、节日以及大型饮宴娱乐活动的时候,总会看到那些载歌载舞的珊蛮巫师们的身影。做为早期蒙古人中率先掌握各种文化知识的他们,普遍受到无比的尊崇与敬畏,即使是在成吉思汗时代,他们在民众心目之中依旧保有强大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力都或多或少得与那些富于哲理,悠扬动听的赞祝词难以分开。
在蒙古人看来,能够得到珊蛮巫师吟诵祝福是无比吉祥的象征,这种传承于上古神话传说,内容欢畅,形式上首韵互和,通俗易懂,平实可亲、琅琅上口的歌词,会传达长生天神的意愿,为牧民的心灵带领安宁平和并保佑阖家人畜平安。
蒙古赞祝词的内容的取材也是十分广泛的,其中不仅包括歌颂上古神灵、人类英雄业绩、天体气候变化、山川风物沿革等等恢宏壮阔的大事,也有对自然现象、风物景色、放牧生活、野兽家畜、起居饮食、日常生活、风土人情等等细节方面的描述评说,既体现了早期神秘主义的特色,又充满了人文写实色彩,因而为广大蒙古人民所喜闻乐见。下面,将从其中选结一二,做为例证。
摔跤手赞
从七勃里(外)挥舞而来,
震得地动山摇;
从八勃里(外)挥舞而来,
踏得山川颤抖;
咆哮着狂舞而至,
越舞越有力气。
从前面猛看过去,
犹如一只斑虎;
从后面乍看过去,
牵浩一头狸虎。
他有雄狮般的力气,
他有巨象般的身躯。
这摔跤手的技巧啊,
实在令人惊奇。
(选自色道儿吉义编译《蒙古族历代文学作品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2,P52)
众所周知,摔跤、射箭与马术为蒙古族的“男人三绝”,而摔跤在其尤站胜场。通常,一名优秀的摔跤手在人们心目之中就是男子汉的典范。在古代蒙古,摔跤不仅是庆典上奉献给神灵的表演,同时也是男人之间解决彼此恩怨的一种决斗方式。比如成吉思汗就曾经命令他的弟弟别勒古台与伤害过他不里孛阔要求通过摔跤做为决斗方式,而成吉思汗的另一个幼弟帖木格则向阔阔出提出以摔跤的方式了解二人之间的恩怨。通过这些历史上著名的决斗场面,足以确定摔跤一术在蒙古人心目之中的至高地位。因此,如上这样一首歌颂摔跤手的赞祝词的出现,也绝非孤立的现象。在这首词中,那位迭名作者不惜采取夸张、比喻等等手法,用集尽溢美的赞颂之词,将一位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摔跤手步入场地之时的种种行动、表情刻划得细致入微,令读者不禁产生了身临其境的感觉。
骏马赞
它那飘飘欲舞的轻美长鬃,
好像闪闪发光的金桑烘风旋转;
它那炯炯发光的两只眼睛,
好像一对金鱼在水中游玩;
它那宽阔无比的胸膛,
好像滴满了甘露的宝壶;
它那精神抖擞的两只耳朵,
好像山顶上盛开的莲花瓣;
它那震动大地的响亮回音,
好像动听的海螺发出的吼声;
它那宽敞而舒适的鼻孔,
好像巧人编织的盘肠;
它那潇洒而秀气的尾巴,
好像色调醒目的彩绸;
它那坚硬的四只圆蹄,
好像风驰电掣的风火轮;
它全力汇聚了八宝的形状,
这神奇的骏马啊,真是举世无双。
(见前引书,P48)
蒙古族是马背上的民族,马之于人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因此,它们也是蒙古人心中最为重要的存在,因此赞颂其丰姿仪态的作品也为数甚多。做为重要的交通工具和战争资源,马的形象渗透了蒙古人的全部生活,甚至形容一个人的优秀,也往往比之于马,例如成吉思汗麾下的四位名将——博儿术、木华黎、赤老温、孛罗兀勒就有这“四骏”之美名。再看这首赞词,其中运用了大量的排比句式来描述骏马的各个部位,每一处都以另一种美好的事物来加以比喻形容,突显了骏马奔走时的健美体态和迅捷速度。而如此形象隽永的词句,则将作者对马的喜爱之情表露无遗,也正因其倾心歌颂的真情实感,使得一匹骏马的血肉灵魂尽展于读者的面前,其鲜活灵动的形象呼之欲出。
也就是在这段文化大发展的时期,通常意义上的诗创造也渐渐萌芽并迅速达到了鼎盛时期。根据波斯学者们的记述,蒙古人喜欢通过诗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内心情感和思想,采取抒情诗方式来展现个人意愿的形式已经成为了当时的一种普遍现象。这其中最具代表意义的文字类作品就是人称“天下奇书”的《蒙古秘史》(关于这部具有多方面价值的巨著的具体情况,将在专门章节之中做出介绍)。因此,也可以这样说,《秘史》本身就是一部纪元十二至十三世纪的蒙古诗歌总集。据统计,全书共收录诗作122首,而就其通常分段来看,228段的文字之中几乎每两段就有一首诗作,其出现频率之高亦无愧于诗集之称。
书中的诗歌,风格多样,内容广泛,可分为:叙人、记事、外交词令、讽刺小品、赞歌、哲理训诫、誓词、规劝词等等形式。其作者上迄成吉思汗,下至无名的草原诗人,可谓函概了当时蒙古社会的各个层面。这些诗句,或雄浑激扬,或苍凉古朴,或情深意切,或风趣幽默,遣词别致,意境深刻,行文流畅,修辞考究,表现了一个民族在其上升期内所表现出来的智慧与自信。
做为一个民族的历史与未来的代表,史诗在文学与历史上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蒙古族的史诗同样具有丰富的文化底蕴和身后的历史积淀。200年来,世界各国的学者们无不为其着迷,经过悉心搜集和整理,现在已知的蒙古族史诗数量竟然高达300余首(剔除其中变体部分,亦不下80部),其数量之多,在世界各民族文学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如此卷帙浩繁的史诗,既是研究蒙古历史的不可多得的第一手材料,也为古代世界文学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也是蒙古族文化的骄傲。
在众多史诗之中,以英雄史诗类型的作品为最,民间通常称其为“镇压蟒古斯的故事”。根据其篇幅,学者将其分类为“单本史诗”和“长篇传记史诗”。就其生成年代,目前学界尚无准确的定论,只是将其大体的时间范围圈定为奴隶社会阶段,这种结论完全源自那个时期全世界普遍的英雄崇拜思想的共性而言,其繁荣阶段应不晚于《蒙古秘史》,主要的传播载体依旧保留于说唱艺人的口头。当然,这其中很多作品本身就属于民间口头创作。
所谓蟒古斯,是蒙古神话之中最大的恶魔,它有着无数个凶恶丑陋的头颅,代表世间一切黑暗、丑恶、愚昧与罪行,凝聚了无比强大的邪恶之力,是一切善良、正义与美好事务的对立面。然而,在蒙古人的心目之中,与之发生对决的却不是神灵,而是来自人类之中的英雄。可见,此时的蒙古人已经通过与严酷自然的搏斗,人文意识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从而摆脱了蒙昧期的惟神论的影响,转而崇敬起来自同类之中的优秀人物。来自人群之中的“把阿秃儿”们成为了赞颂的主体,他们高举神奇的武器,骑乘神骏的良驹,发挥自身的高超技艺和绝顶智慧,一次又一次地击败了来自恶魔“蟒古斯”的侵袭,保护了自己的人民,从而赢得了无限的敬仰,也就此成为作品之中被加以浓墨重彩描述的核心人物。
这些英雄不仅精通“男子三绝”,更具备诸如忠诚、勇猛、善良,正直等等一切人类最高的美德,同时,他们也会在对抗邪恶的征途中遇到各种各样的人物,还会因此与美丽温柔的牧羊女发生纯洁真挚的爱情。人性化的描写使得他们摆脱了神格,而化作一个又一个有血有肉、形象丰满、可敬可亲的形象。他们的胜利,往往并非一人之力,总是得到各种力量的协助,显得真实生动,同时也反映了当时的人们在自然压力之下的不屈精神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诚然,这些英雄也有着与众不同的出身和超越常识的本领:他们吃饭的时候用七十人才能抬动的大碗,可以举起牛犊大小的巨石去击打敌人,坐骑的鞍子放在地面上就像一座小山。他们因为自身力量的强大,因而产生了无比的自信。他们认为自己的身体是“父母给予的”,与任何神的恩赐无关,于是他们屡次击败恶魔“蟒古斯”的功绩也只能属于自己,而并非天意相助。他们摆脱了对天的敬畏,甚至公然发出挑战苍天的声音,为了“与腾格里神战斗而生”(《汗哈仍贵》)#蝴们敢于蔑视神权,挑战巫师(《古诺干勇士》),甚至为了保卫自己的爱人而与神发生殊死搏斗,并取得最终的胜利(《青格勒汗》)。由此可见,史诗的出现标志着神权思想的解体,直到十七世纪黄教传入前,蒙古人的思想领域之中充满了浪漫主义和人文主义的思想。
史诗的表现手法相当自由,而去相当注意情节之上的起承转合,具有相当精强的故事性与可读性。它的写作往往围绕着一个中心来展开情节,又于其中穿插了一些与之相关的其它小故事,当高氵朝情节即将来临之前,又很巧妙的安排下一些小高氵朝,以大海升波之势层层递进,步步铺垫,将整个故事自然而然的推上了华彩颠峰。使听众于满足娱乐感观之余,又感合情合理,毫无突兀之感。同时,说唱者通过自己的语言功力和音乐衬托,将听众带入到故事情节之中,身临其境之感油然而生。
做为民间艺术的典型代表,史诗摆脱了韵文体诗歌的拘束,还原了蒙古人最初的自由文学题材,摒弃了渲染神秘主义的晦涩语句和呆板格式,以通俗生动的语言和灵活多变的风格浸入人类生活之中的各个思想领域,为蒙古语言文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