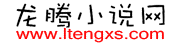暗夜笼罩下的中都城,战马嘶鸣,刀剑钪镪,垂死者的呻吟,妇孺们的惨号,加之在城中各处无情肆虐的烈火飞烟,将这做华北第一繁华都会化做了修罗世界,人间炼狱。
整座城市中,唯一还不曾遭受战火荼毒的只有位于西山龙泉寺。此时,那位被郭宝玉评价为人中龙凤的耶律楚材正站在寺庙的致高点舍利宝塔的顶楼,驻足凭栏,以一种悲怆与愤恨杂揉的目光凝视着眼前这片惨遭蹂躏的土地。
他身处的这座宝塔内,供奉着佛祖释尊寂灭后留下的佛牙舍利子——佛家的无上圣物。此宝从天竺流传至西域,由南北朝时代发大愿力西行求法的名僧法显大师辗转带回,此后常驻于中原大地,历经朝代更叠,终为前代建都于北京的契丹人所获。笃信佛法的丞相耶律仁先的母亲燕国太夫人郑氏,遂在西山建此龙泉寺,并建下这一座八角十层的砖塔供奉此宝。可以说,这里凝聚着那位崇尚和平、仁爱的佛陀的精魂,却目睹了这人世间屈指可数的杀戮与毁灭。
可以想象,象耶律楚材这样一位虔诚的佛教信徒居然处身于这精神世界的圣地之中,来面对这一幕繁荣文明被无情摧残,生灵如牛羊般任人屠戮的惨剧,他的心情会是何等痛苦悲凉。每当城中有撕心裂肺的哀呼或建筑物颓然倾倒的轰鸣传入他的耳鼓,他的面部肌肉就会产生一阵痉挛,表面的镇静也只是为了压抑内心汹涌澎湃,一浪高过一浪的波涛。
忽然,寺院大门方向传来了一阵骚动,楚材隐隐听到有人在用蒙古话叫骂着,他心中一动,轻轻的说了两个字:"来了!"便转身大步行下塔去。方出塔门,迎面正遇到了本寺的一位僧人慌慌张张得跑过来。他一见楚材,连忙叫着他的别号说道:"湛然居士,前门有些鞑子由一汉人引着,口口声声说他们的大汗要招见你,想来必无善意,方丈大师要我来通知你,快从后门逃走吧。"
楚材神色镇定得说道:"多谢方丈大师的盛情,但我不能逃。我若逃了,鞑子必然迁怒于本寺,到时杀害僧众,毁弃佛宝,楚材岂非成了佛门罪人?佛云,‘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待我去会会这些凶徒!"
说罢,他略无犹豫,大步向前,行至寺门前用蒙古语大声喝道:"休得为难僧众,你们要找的耶律楚材在此!"
洞开的寺门前,松明火把照如白昼,百余名全副武装的蒙古军整齐列立,为首一将盔甲鲜明,看容貌却有些面善,楚材一时记不得在哪里见过。那将却面带微笑,迎上前来拱拳拱手道:"晋卿兄别来无恙?"
"郭兄?怎么会是你?你真得降了蒙古人?"耶律楚才认出了郭宝玉。
"成吉思汗一代雄主,方兴未艾,伐暴金以拯天下,正是我辈一心盼望的明主。大汗求贤若渴,闻晋卿兄之大才,便特命小弟前来相请。"郭宝玉道。
"嘿嘿!暴金!雄主!"楚材冷笑道,"蒙古之暴更胜于金,还奢谈什么拯天下?他们的行径比之盗匪和凶手只怕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吧?我耶律楚材岂能与这等残暴之人为伍?!"
"晋卿兄慎言!"郭宝玉面色陡变。
"怕什么!大不了一死而已,有何惧哉?"耶律楚材气势凛然,厉声喝问道,"他不是要见我吗?好!我倒要看看这个杀人魔王长得什么样!"
"这……晋卿兄若是这种见法,那还是不见的好。"郭宝玉沉吟道。
耶律楚材神情肃然得遥望山下,火势已渐渐烧近,喊杀声也显得愈发清晰。他大声道:"我这一去,早将生死置之度外。但求能救这一方百姓,为这百年京华留下一线生机,虽粉身碎骨,又有何憾!走吧,不要再耽搁了。"
※※※ ※※※ ※※※
桓州,蒙古军的大营。
驻跸于此的成吉思已经得到了中都落城与完颜福兴自尽这两个消息。在他印象里,这位死守孤城长达一年之久的老将是一位才能出众,人品贵重的良才。虽然他多次拒绝了自己的劝降,却唯其如此方显出他那可敬可佩的忠贞品格。因此,他曾传令于木华黎等人,城破后勿必要将这位忠勇的老人平安得带到自己面前,即使他不投降,也不想伤害他的性命。
福兴的自尽使得成吉思汗联想到另外一位人物——乃蛮老将可克薛兀撒卜剌黑。双方年纪相当,品格亦有诸多相似之处,包括为自己准备的退场方式,都是如出一辙。这是一种怎样的思维呢?为何会引导他们面不改色地走向死亡呢?既便刃断弓折,就必须走上这样一条绝路吗?成吉思汗自问无意将这两位老将逼迫至死,而这种情况实是平生所不多见的。
较之福兴之死,中都城中的大火却并不能打动成吉思汗的心。也许是他在初生之际就遭遇过火灾吧,反而对火的颜色没有太多的好奇之心。他甚至可以想象得到,那火有着怎样的颜色,引燃建筑之后又会发出何种声音。但是,他依旧没有枉驾一观战果的打算,只是派遣汪古儿、阿儿孩与失乞忽都忽这三个人代表自己去接收金廷府库里的珍宝,即金银珠宝以及郭宝玉和明安口中反复提及的人才。
正当他对福兴之死辗转冥思,不得要领之际,纳牙阿走入帐内向他禀报了郭宝玉与耶律楚材到来的消息。
"好!我要亲自在宫帐外迎接这位神奇的客人。"
成吉思汗想,即然失去了福兴这样的人才,那么能得到楚材也算是一种补偿——如果他真得如郭宝玉所描述的那样了不起的话。
宫帐之外,耶律楚材那如武人般长大的身姿昂然挺立,长长的美髯迎着塞上烈风飘逸飞扬,于儒雅的气度之中又有三分凛然锐气。
真威风啊!成吉思汗从看到他的第一眼起就喜欢上了这个人。他没有立刻说什么,却示意身边的怯薛歹们上前去同他比个头儿,包括纳牙阿在内的众人最多也只抵到他的肩头。对于这种有些古怪的举动,楚材却能安之若素,神态自若,丝毫没有畏葸之意。这份镇定又令成吉思汗的心中增添了几分好感。
他微笑着走上前来,打量着他,尤其关注着他那副从双颊蓄到下巴的浓黑胡子,认为这是自己所看到过的最漂亮的胡子。对此,他甚至产生了想亲手摸一摸的冲动。不过,他还是抑制住了这种会被对方误认为侮辱的举动。
他问楚材:"你多大了?"
"二十六岁。"楚材用明朗有力的声音回答道。
"很年轻啊!"
成吉思汗赞叹着。对于他居然可以流利得听说蒙古语,令他颇感高兴。
"你是个人才!我在一年前就听说你是契丹人之中的豪杰。过去,你的祖国契丹被金国人所灭,如今正在我蒙古的帮助下恢复独立,你这样的人才正该投入到这伟大的民族复兴运动之中去啊。"
在契丹人面前,成吉思汗一惯善于将自己打扮成为复仇者的形象,因此获得了包括耶律留哥、阿海、石抹明安等一批同盟者的助力。如今,面对楚材,他再度施展出这个高明的手腕,希图一举掠获对方的心。
然而,楚材的回答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可汗大人的话,在下未敢苟同。我家三代侍奉于金国,自当忠诚以事之,又怎敢将君父当作寇仇呢?那样岂非是不忠不义,欺君妄上的小人佞臣么?"
一旁的郭宝玉闻言大惊,连忙向他频施眼色。楚材对此却视而不见,继续以他那铿锵有力的口调侃侃而谈道:
"请问大汗,你既然口口声声说是来为契丹人与汉人报仇,可是你的士兵却正在毁坏汉人与契丹人的城市、房屋、农田,劫掠他们的妇女、财物、牲畜。这就是所谓的复仇吗?如果是这样,那么你们与所谓的暴金又有何不同?"
"大胆!竟敢将大汗与暴金相提并论!"纳牙阿断喝一声,同时钢刀出鞘。
刀光闪闪,寒气逼人,近在身侧,只需大汗一个微小的手式,便可随时夺取楚材的生命,但他却连眼角都不搭,明亮的眼神直迫成吉思汗,朗声喝道:
"在金国的治下,百姓尚且可以平静得生活下去,而你们一来,便要让他们丧失一切,流离失所,这便是伟大的解放运动吗?你们其实连暴金也不如!"
"劫掠是游牧人的传统!是士兵们的特权!"纳牙阿大声抗辩道,"把这个狂妄的疯子抓起来!"
"让他把话说完!"成吉思汗以低沉威严的声音制止了纳牙阿。
"何谓暴?残民以逞者谓之暴!因此,残害民众者都是那些有权有势的当政者!"
一向谦和温良的楚材此时俨然化做了一只暴怒的狮子,激烈如枪刺箭簇般的话语配合着胸前的戟张的长须,夺人之气溢于颜表#蝴的心情从未如今日这般舒畅,多年来郁积于胸中的对朝政的不满、对国势的担忧、对民生的悲悯,竟能于此时此地,在一个异族首领的面前得以一吐为快。这是何等酣畅淋漓的快意啊。
在金国,他不过是一介员外郎的散官,在那衮衮诸公林立的庙堂之上根本没有发言权。唯有今日,他却得到了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面折庭争。
"蒙古所仇者应该是金国的皇帝与官吏,而非那些无拳无勇的天下苍生。大汗如今每至一地,动辄屠城焚屋、纵兵劫掠,还美其名曰‘传统、权力‘。岂不闻,‘十里不同天,五里不同俗‘,那样的传统和权力也许在草原上可以行得通,可这里是中原!要想成为中原之主,就要按照中原的规模行事!"
"那中原的规矩又是什么呢?"
众人惊诧得发现,大汗居然在向这个大放厥词的契丹人求教。这诚挚的态度使楚材的语气也和缓了下来。适才他自份必死,因此口调激烈,此时见对方虚心求教,他的回答便趋于理性陈述了。
"中原与草原的区别就在于城市。城市是什么呢?是人类文化、艺术、知识、财富的集合体。一座城市所能出产的财富是几万只牛羊都无法比拟的,而它所代表的人类最高级的思想,更是不可以黄金的价格来衡量……"
成吉思汗认真得倾听着这些对他来说都是前所未闻的事情。正像所有其他的蒙古人一样,他根本不懂什么城市经济,对城市经济没有任何概念;至少在他一生中的这个阶段,他还不知道除了把被攻陷的城市摧毁以外,还可以利用占领的城市做其他的事情。如果说父亲也速该与军师月忽难先后为他开启了对广大世界与伟大文明的认知之门的一角,使他得以管窥到其内的一缕春光的话,那么如今的耶律楚才则是以他那远胜于前两者的卓越才识,亲手为他洞开了这扇沉封已久的大门,使其中那无限明媚的春光乍然倾泄于他的面前,扑入他的怀中。
此后的三天内,成吉思汗便将楚材留在宫帐内通宵达旦得闭门倾谈,他下令除了吃饭时间外,任何人不得打扰他们。在这三天里,两个人都象着了魔一样,多半是在饥肠辘辘的情况下才会发现送入的饭菜已经冰凉;实在困倦了就随便斜靠在哪里打个盹。他们的外表开始憔悴,但都在彼此的目光之中看到了智慧与知识的火花。
在第三天的深夜里,成吉思汗向楚材询问起关于福兴之死的话题。楚材低下头想了想,回答道:
"这是汉文化对于执政者的一种要求。文死谏,武死战,国君死社稷,这是每个合格的君王与臣下都必须尽到的责任。文官在向君王进言的时候,要不避生死,实话实说;武将在为国作战时,也要有捐躯报国的觉悟;至于君王,则要将自己的生命与国家的兴亡牢固得维系在一起。只有这样,大家才可以同心协力,使国家内享安定繁荣,外御侵略之忧。"
成吉思汗仔细得品味着楚材的话,点头道:"你说的对,大家都要为这个国家尽责。象完颜旬那样抛弃中都的君主就是失职,而象福兴这样的人则是尽责。楚材,我希望你留在我的身边,为蒙古人讲出这些理道,使他们的心中也永远记住自己的责任,同时也随时解答我的疑问和提醒我对自身责任的遗漏,你肯吗?"
成吉思汗终于在最恰当的时刻说出了自己的最终目的,他以灼热的目光凝望着楚材的眼睛,这目光有洞辙对方肺腑的魔力。
楚材没有犹豫、没有沉吟、更没有丝毫停顿得回答道:
"愿效犬马之劳!"
"好!从今以后,蒙古人的队列中又多了一位乌托合撒儿(1)。"
一切不着痕迹,一切水到渠成。从此,一代天骄的身边多了一位富有良能的大臣。这位来自敌人营垒中的人以他那高尚的忠君情操、渊博的知识、出色的才干,赢得了成吉思汗的敬重与信任。当这一决定遭到许多重臣的置疑时,成吉思汗也不曾有丝毫动摇。他援引过去的往事来说服反对者们:
"收降伏为臣下,这也算一种危险吗?为我战死疆场的那些人之中,又有多少是最初追随于我的人呢?如果我的器量足够容纳别人,那么任何降伏者都将成为蒙古的箭簇!"
显然,这最后一句是在特指者别。
为了打消众人的疑虑,成吉思汗命楚材向众人展现他那高超的占卜之术。所谓占卜,就是牛羊的肩胛骨放入火堆中炙烤上一定时间后,再取出观察骨头上被火烧出的裂纹纹理,据此判断吉凶事。此前,在推举成吉思汗的大会上,那位通天巫曾经表演过,可见这种占卜方式在蒙古族中间相当流行。楚材的占卜结果,每次有非常灵验,很快便成为了蒙古军中不可或缺的人物。后来,每当远征之前便要请楚材来占卜吉凶胜负便成为了蒙古军中一条不成文的规定。
当然,楚材绝非有未卜先知之能的神仙。他的那些预言来自于丰富的学识、过人的才智和对人心的准确把握。同时,做为一名虔诚的佛教徒,他也有着悲天悯人的心肠。他准确地判断出成吉思汗绝非生性残暴的恶魔,他的那些破坏杀戮完全是源于对城市文明的不解,因此他决心借助神佛的名义来设法对成吉思汗施加影响,从而引导他走上文明之路,减少战争对平民的损失。
在成为大汗的谋臣之后,他就立刻提出了第一个请求:
"是否可以停止对城市的破坏和掠夺呢?我会证明,城市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它所给予大汗的回报,将会有百倍于掠夺的效果。"
"能试着谈谈这种效果吗?"成吉思汗问道。
"耕地是可以产出粮食的,而且产量一定会高于放牧。中原的财富,很大一部分都是来源于农耕,大汗若想要蒙古富强,完全可以让农民去耕种土地,然后向他们征收税款。这种税收将是源源不断,永远不会枯竭的宝库!"
"还有什么?"
"还有知识!知识有着改变命运的神奇功效。将有知识的人保护起来,再按照其特长安排到合理的岗位上,让他们去为大汗管理国家,那么民心将稳定,税收将增加!天下,可以在马背上得到,但是绝不能通过马背去治理!"
楚材的进言,无疑打动了成吉思汗的内心。在政治上,他有着超乎寻常的悟性,因此很快便感受到这些进言之中有着很大一部分可取的因素。也正是通过这些反复的磋商与交流,使得他愈来愈信服楚材的才智与品性。诚然,这种改变并非一朝一夕间就会产生立竿见影的成果,但是在楚材的力争与建议之下,许多野蛮的命令被改变了,确也是不争的事实。
与此同时,楚材也渐渐感受到成吉思汗身上那种非凡的魅力。从未有一位征服者会如此热情地听取被征服者的言论,并最大程度得去采纳其中可以理解的成份。即使这位主君与自己有着不可逾越的文化鸿沟,却并不妨碍彼此之间建立起一种互相信任的友好情感。至少,在楚材看来,历代王者之中能如此虚心听取不同意见的并不多见。他也就愈发坚信自己最初的选择是正确的。
根据楚材的建议,成吉思汗派人向先前派往中都负责处理战后事宜的三位部下传达了改变以往接收模式的新令谕:
金国士兵和一般市民以及中都城内所有的人,除战死者之外,全部集中到郊外的一个地方。对于这些俘虏,不再象从前那样首先挑选女人,将她们用绳索串连起来送往大本营。而是优先从男子中选出具有特殊技术和教养的人。
他还在令谕末尾严格告诫部下:对待这些男子不可感情用事,即使是抱有强烈敌对情绪的人,只要是有特殊技术和教养,一律送往自己的营地来。
接受到命令的失乞忽都忽一丝不苟得尊照执行起来。于是,连续多日之间,蒙古大营中就会出现这样一副无序循环的情景:
各种种族不同,打扮各异的人混杂在运送财帛的驮马队中走来。无论他们是顺从还是反抗,都不会遭到杀害,最多是被扭住胳膊,押回队列而已。在这样的行列之中,有最受欢迎的能工巧匠,有富于经验的武将士兵,还有一些稀奇古怪的出家人、占卜师、医生、法官、农夫和儒生。对于最后一种人,成吉思汗完全不知道他们的用处,只是命令由楚材来接待。
很快的,成吉思汗发现了一个要命的问题,那位终于职守的六弟居然真的没有送来任何一名年轻妇女。有的只是一些上了年纪的老妇,这自然不对成吉思汗的胃口。
"这些老太太是干嘛的?"
成吉思汗向解送者询问道。
"据说是产婆,懂得怎样顺利的接生孩子。"怯薛歹们回答。
成吉思汗的眼前立刻浮现出失乞忽都忽那张刻写着一丝不苟的面容,严肃、冷静得近乎淡漠的表情。
"真是哭笑不得啊。"
他这样想着,轻轻摇了摇头。然则,对于这种行为,他并不排斥,尤其是念及此前不久有人向自己汇报的那件贿赂案中这位"六弟"所表现出的廉洁操守,他的脸上又浮现起一丝欣慰。
事情就发生在三人察点府库的时候。负责镇守府库的是一位名叫合答的降将,为了讨好这三位蒙古将官,他取了几件绣金丝织品作为个人战利品赠送给他们三人。这种绣金丝织品相当名贵,那个世纪末,马可.波罗曾对这种织品赞叹不已。阿儿孩和汪古儿为这种名贵织品所吸引,便收下了礼物,唯有失乞忽都忽严辞拒绝:
"过去,这里的一切都属于阿勒坛汗;如今,这些都归于成吉思汗。你有什么权力擅自支配属于成吉思汗的财产?又怎敢擅取此物来送与我?我决不接受此物!"
通过这件事,成吉思汗深切得感到一种叫做腐败的文明副产物凭籍着人类性格之中的贪欲之心。三位使者之中的两位都受到了腐蚀,这就足以证明这种副产物的可怕之处,它正在逐步侵蚀着蒙古狼们的心灵,进而控制他们的精神,弱化他们的斗志。这种潜移默化的改变实在是比战场上面对敌人的百万大军更为凶险难防。
这位一代天骄在大胜之后,首先想到的不是弹冠相庆,而是找出自己的国家与军队之中还存在着哪些不足,又如何使之得以补完加强。他打定主意,一定要严厉惩罚行贿与受贿者,更要大张旗鼓得褒奖识大体、慎职守的忠诚之士,要让全体蒙古人都以失乞忽都忽为凯模,学习他廉洁自律的美德,更加忠诚于自己,忠诚于大蒙古的事业,而不至走上阿勒坛汗的败亡之路!
对于苟延残喘于黄河之南的金国,成吉思汗准备充分利用攻陷北京所造成的有利形势,一鼓作气得将其消灭,但那条叫做黄河的大河对于骑兵来说过于宽阔了,也是短时间内无法超越的一条天堑。虽然在征伐西夏时,他曾经见过这条河的上游,但是看到下游的时候,他还是无法将这两者统一起来。这条河在此地如同被天神的巨斧突然劈开一般,不可思议得向两边阔展出许多。而那湍急的河水,即使看上一阵都会令人的头晕目眩。
就如何通过黄河的问题,成吉思汗召开了军议。他特别征询了郭宝玉与耶律楚材的意见,二人都指出现在渡河作战是不可行的,因为难以短期内征集到足够的船只来运渡大军。若以小股部队进攻,则很难占到便宜。真正的大规模渡河作战只能等到冬天黄河结冰的时候才能展开,那时战马可踏过冰面进攻敌人。成吉思汗对此深以为然。他命楚材进行占卜,以确定未来的进军方向。楚材拿起被火焚烧过的羊骨,仔细观察上面的裂纹,然后抬起头来说道:
"臣昨晚夜观天象,见那象征着战争的长庚星出现在西北的天幕上;现在又根据这块羊骨上显示出来的征兆看来,在那个方向正有一位大汗的宿仇在蠢蠢欲动。"
"西北?指的是哪里?哈剌契丹?"
"是的。"
"那金国怎么办?就任他们恢复起来吗?"
"不,大汗对金的战争不能停顿,但也不能操之过急。"楚材缓缓得说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金国如今虽然衰败,但余势未尽,依旧不可放松。大汗应派一员上将统领中原之兵,采取稳扎稳打的战术,步步为营,一点点得蚕食金国,令其不得休息……"
一名怯薛歹的疾奔而入打断了楚材的话语。他向成吉思汗汇报了来自蒙古的重要消息:——
已故塔阳汗的儿子,丧失了国家的王子屈出律已经流浪到了哈剌契丹国,并得到该国古儿汗直鲁古的收留并将女儿嫁予他。谁知此人得志即猖狂,突然袭击了他的岳父,夺占了整个国家,并与西方回教大国花拉子模结成反蒙古同盟。现在,他正发兵攻打成吉思汗在西域地区的两个盟友:阿儿思兰汗和回鹘部亦都护。前者已经遭其攻灭并杀害,后者的处境亦岌岌可危。他还在西辽国内强行推广自己所信奉的景教,大肆杀害回教徒,实行血腥统治。
"西方的战鼓真得响起来了!"成吉思汗大声道,"漏网的残敌正在对我们磨刀霍霍!我将回师蒙古,然后立刻出兵讨伐屈出律,定要将这条祸根一举斩断!"
"诺!"蒙古众将起立,齐声凛尊。
成吉思汗郑重得说道:"对阿勒坛汗的战争也不能中止。三合木,我命你率军迂回山西,当冬天之时,从黄河最窄的地方踏冰而过,进入陕西,再折而向东,直取南京(开封)!"
"诺!"
奉令的三木合把阿秃儿是蒙古军中的后起之秀。这位年轻的武将在这次中都攻略战中建立了卓越的武勋,任命他为攻击部队长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合身的铠甲紧紧贴在他那匀称的肢体上,益发显出精悍干练的刚阳之气。他用兵擅长快攻,手下的部队有着无坚不摧的攻击力,但在防守战上,则略嫌欠缺耐性和韧性。不过,做为突击部队,这样的缺陷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这是他首次以总大将的身份独当一面,因此在任务的沉重感之外更有着跃跃欲试的欢喜与渴望。因此,他在得到命令后立刻于翌日发兵西行,在翌年(纪元1216年至1217年)冬天强渡山、陕两省之间的黄河,出其不意地袭取了古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古代的长安,现在名叫西安的大城市。此后,他挥军从东进潼关,却在这座天然险隘面前遭到了强力阻击。
在渭水汇入黄河的河口地区,拔地而起的山峦群峰形成了天然的障碍,尤其是那座被称为中原五大名岳之一的华山,更是高不可攀。它与北面的黄河形成了一条狭窄的地峡,潼关就是建立于其中,号称难攻不落的关隘。
三木合把阿秃儿在攻关受挫的情况下不敢恋战,立刻转而向南,通过一条人迹罕至的小道绕过华山,直取另一著名的古都洛阳。然而,洛阳方面也有了森严的防御,使得他无隙可乘。为了防止遭到反包围,三木合放弃了攻城的打算,快速向南进发,进入嵩山山脉。这里的地形之险峻绝不稍逊于华山,却恰巧是金国河南防御阵线的一个漏洞。在经历了艰苦跋涉之后,突然出现在汝南平原上,并一举攻陷了汝州和密州(2)这两座城市。从这里出发向北,完全是坦荡如砥的冲击平原,快马奔行之下,毋需几日即可直薄金国的新都开封城下。
这是一次成功的迂回作战行动,充分展现了三木合灵活多变,大胆巧妙的指挥才能。然而,他在嵩山之中耗费的时间过于漫长,以至于给予金国军队充分的布防时间。各路勤王兵马齐聚都城之下,尤其以山东民兵花帽军最为强悍。他们不仅有作战的实力,更有满腔对蹂躏他们家园的蒙古军的痛恨。因此,他们士气高昂地列阵于开封之南二十公里处的杏花营,对三木合军展开了强力阻击。
眼见急切间难以战胜敌军,三木合果断地下达了退兵令。事实证明,他的决定是相当明智的。就在蒙古军刚刚向西退却后不久,数支金军从几个方向包抄而来,险些形成合围态势。
跳出包围圈的蒙古军不敢再在河南地区停留,他们飞快地向西北而去,来到了陕州(3)境内的黄河岸边。不甘心就此放过蒙古军的金军随后追击,试图在河边再度包围敌人。然而,当他们来到河边才发现,这支给他们带来极大麻烦的敌军已经踏过冰封雪冻的河面扬长而去。
当三木合把阿秃儿进行他那艰苦卓绝的千里作战之时,成吉思汗已经率领大军北归大漠。他的目光已经从南方的金国转向了另一个世界——阿勒坛山以西的广大的未知的世界……——
(1)蒙语,意为长髯公。
(2)汝州,今河南临汝;密州,今河南新密。
(3)陕州,今河南三门峡。
整座城市中,唯一还不曾遭受战火荼毒的只有位于西山龙泉寺。此时,那位被郭宝玉评价为人中龙凤的耶律楚材正站在寺庙的致高点舍利宝塔的顶楼,驻足凭栏,以一种悲怆与愤恨杂揉的目光凝视着眼前这片惨遭蹂躏的土地。
他身处的这座宝塔内,供奉着佛祖释尊寂灭后留下的佛牙舍利子——佛家的无上圣物。此宝从天竺流传至西域,由南北朝时代发大愿力西行求法的名僧法显大师辗转带回,此后常驻于中原大地,历经朝代更叠,终为前代建都于北京的契丹人所获。笃信佛法的丞相耶律仁先的母亲燕国太夫人郑氏,遂在西山建此龙泉寺,并建下这一座八角十层的砖塔供奉此宝。可以说,这里凝聚着那位崇尚和平、仁爱的佛陀的精魂,却目睹了这人世间屈指可数的杀戮与毁灭。
可以想象,象耶律楚材这样一位虔诚的佛教信徒居然处身于这精神世界的圣地之中,来面对这一幕繁荣文明被无情摧残,生灵如牛羊般任人屠戮的惨剧,他的心情会是何等痛苦悲凉。每当城中有撕心裂肺的哀呼或建筑物颓然倾倒的轰鸣传入他的耳鼓,他的面部肌肉就会产生一阵痉挛,表面的镇静也只是为了压抑内心汹涌澎湃,一浪高过一浪的波涛。
忽然,寺院大门方向传来了一阵骚动,楚材隐隐听到有人在用蒙古话叫骂着,他心中一动,轻轻的说了两个字:"来了!"便转身大步行下塔去。方出塔门,迎面正遇到了本寺的一位僧人慌慌张张得跑过来。他一见楚材,连忙叫着他的别号说道:"湛然居士,前门有些鞑子由一汉人引着,口口声声说他们的大汗要招见你,想来必无善意,方丈大师要我来通知你,快从后门逃走吧。"
楚材神色镇定得说道:"多谢方丈大师的盛情,但我不能逃。我若逃了,鞑子必然迁怒于本寺,到时杀害僧众,毁弃佛宝,楚材岂非成了佛门罪人?佛云,‘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待我去会会这些凶徒!"
说罢,他略无犹豫,大步向前,行至寺门前用蒙古语大声喝道:"休得为难僧众,你们要找的耶律楚材在此!"
洞开的寺门前,松明火把照如白昼,百余名全副武装的蒙古军整齐列立,为首一将盔甲鲜明,看容貌却有些面善,楚材一时记不得在哪里见过。那将却面带微笑,迎上前来拱拳拱手道:"晋卿兄别来无恙?"
"郭兄?怎么会是你?你真得降了蒙古人?"耶律楚才认出了郭宝玉。
"成吉思汗一代雄主,方兴未艾,伐暴金以拯天下,正是我辈一心盼望的明主。大汗求贤若渴,闻晋卿兄之大才,便特命小弟前来相请。"郭宝玉道。
"嘿嘿!暴金!雄主!"楚材冷笑道,"蒙古之暴更胜于金,还奢谈什么拯天下?他们的行径比之盗匪和凶手只怕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吧?我耶律楚材岂能与这等残暴之人为伍?!"
"晋卿兄慎言!"郭宝玉面色陡变。
"怕什么!大不了一死而已,有何惧哉?"耶律楚材气势凛然,厉声喝问道,"他不是要见我吗?好!我倒要看看这个杀人魔王长得什么样!"
"这……晋卿兄若是这种见法,那还是不见的好。"郭宝玉沉吟道。
耶律楚材神情肃然得遥望山下,火势已渐渐烧近,喊杀声也显得愈发清晰。他大声道:"我这一去,早将生死置之度外。但求能救这一方百姓,为这百年京华留下一线生机,虽粉身碎骨,又有何憾!走吧,不要再耽搁了。"
※※※ ※※※ ※※※
桓州,蒙古军的大营。
驻跸于此的成吉思已经得到了中都落城与完颜福兴自尽这两个消息。在他印象里,这位死守孤城长达一年之久的老将是一位才能出众,人品贵重的良才。虽然他多次拒绝了自己的劝降,却唯其如此方显出他那可敬可佩的忠贞品格。因此,他曾传令于木华黎等人,城破后勿必要将这位忠勇的老人平安得带到自己面前,即使他不投降,也不想伤害他的性命。
福兴的自尽使得成吉思汗联想到另外一位人物——乃蛮老将可克薛兀撒卜剌黑。双方年纪相当,品格亦有诸多相似之处,包括为自己准备的退场方式,都是如出一辙。这是一种怎样的思维呢?为何会引导他们面不改色地走向死亡呢?既便刃断弓折,就必须走上这样一条绝路吗?成吉思汗自问无意将这两位老将逼迫至死,而这种情况实是平生所不多见的。
较之福兴之死,中都城中的大火却并不能打动成吉思汗的心。也许是他在初生之际就遭遇过火灾吧,反而对火的颜色没有太多的好奇之心。他甚至可以想象得到,那火有着怎样的颜色,引燃建筑之后又会发出何种声音。但是,他依旧没有枉驾一观战果的打算,只是派遣汪古儿、阿儿孩与失乞忽都忽这三个人代表自己去接收金廷府库里的珍宝,即金银珠宝以及郭宝玉和明安口中反复提及的人才。
正当他对福兴之死辗转冥思,不得要领之际,纳牙阿走入帐内向他禀报了郭宝玉与耶律楚材到来的消息。
"好!我要亲自在宫帐外迎接这位神奇的客人。"
成吉思汗想,即然失去了福兴这样的人才,那么能得到楚材也算是一种补偿——如果他真得如郭宝玉所描述的那样了不起的话。
宫帐之外,耶律楚材那如武人般长大的身姿昂然挺立,长长的美髯迎着塞上烈风飘逸飞扬,于儒雅的气度之中又有三分凛然锐气。
真威风啊!成吉思汗从看到他的第一眼起就喜欢上了这个人。他没有立刻说什么,却示意身边的怯薛歹们上前去同他比个头儿,包括纳牙阿在内的众人最多也只抵到他的肩头。对于这种有些古怪的举动,楚材却能安之若素,神态自若,丝毫没有畏葸之意。这份镇定又令成吉思汗的心中增添了几分好感。
他微笑着走上前来,打量着他,尤其关注着他那副从双颊蓄到下巴的浓黑胡子,认为这是自己所看到过的最漂亮的胡子。对此,他甚至产生了想亲手摸一摸的冲动。不过,他还是抑制住了这种会被对方误认为侮辱的举动。
他问楚材:"你多大了?"
"二十六岁。"楚材用明朗有力的声音回答道。
"很年轻啊!"
成吉思汗赞叹着。对于他居然可以流利得听说蒙古语,令他颇感高兴。
"你是个人才!我在一年前就听说你是契丹人之中的豪杰。过去,你的祖国契丹被金国人所灭,如今正在我蒙古的帮助下恢复独立,你这样的人才正该投入到这伟大的民族复兴运动之中去啊。"
在契丹人面前,成吉思汗一惯善于将自己打扮成为复仇者的形象,因此获得了包括耶律留哥、阿海、石抹明安等一批同盟者的助力。如今,面对楚材,他再度施展出这个高明的手腕,希图一举掠获对方的心。
然而,楚材的回答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可汗大人的话,在下未敢苟同。我家三代侍奉于金国,自当忠诚以事之,又怎敢将君父当作寇仇呢?那样岂非是不忠不义,欺君妄上的小人佞臣么?"
一旁的郭宝玉闻言大惊,连忙向他频施眼色。楚材对此却视而不见,继续以他那铿锵有力的口调侃侃而谈道:
"请问大汗,你既然口口声声说是来为契丹人与汉人报仇,可是你的士兵却正在毁坏汉人与契丹人的城市、房屋、农田,劫掠他们的妇女、财物、牲畜。这就是所谓的复仇吗?如果是这样,那么你们与所谓的暴金又有何不同?"
"大胆!竟敢将大汗与暴金相提并论!"纳牙阿断喝一声,同时钢刀出鞘。
刀光闪闪,寒气逼人,近在身侧,只需大汗一个微小的手式,便可随时夺取楚材的生命,但他却连眼角都不搭,明亮的眼神直迫成吉思汗,朗声喝道:
"在金国的治下,百姓尚且可以平静得生活下去,而你们一来,便要让他们丧失一切,流离失所,这便是伟大的解放运动吗?你们其实连暴金也不如!"
"劫掠是游牧人的传统!是士兵们的特权!"纳牙阿大声抗辩道,"把这个狂妄的疯子抓起来!"
"让他把话说完!"成吉思汗以低沉威严的声音制止了纳牙阿。
"何谓暴?残民以逞者谓之暴!因此,残害民众者都是那些有权有势的当政者!"
一向谦和温良的楚材此时俨然化做了一只暴怒的狮子,激烈如枪刺箭簇般的话语配合着胸前的戟张的长须,夺人之气溢于颜表#蝴的心情从未如今日这般舒畅,多年来郁积于胸中的对朝政的不满、对国势的担忧、对民生的悲悯,竟能于此时此地,在一个异族首领的面前得以一吐为快。这是何等酣畅淋漓的快意啊。
在金国,他不过是一介员外郎的散官,在那衮衮诸公林立的庙堂之上根本没有发言权。唯有今日,他却得到了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面折庭争。
"蒙古所仇者应该是金国的皇帝与官吏,而非那些无拳无勇的天下苍生。大汗如今每至一地,动辄屠城焚屋、纵兵劫掠,还美其名曰‘传统、权力‘。岂不闻,‘十里不同天,五里不同俗‘,那样的传统和权力也许在草原上可以行得通,可这里是中原!要想成为中原之主,就要按照中原的规模行事!"
"那中原的规矩又是什么呢?"
众人惊诧得发现,大汗居然在向这个大放厥词的契丹人求教。这诚挚的态度使楚材的语气也和缓了下来。适才他自份必死,因此口调激烈,此时见对方虚心求教,他的回答便趋于理性陈述了。
"中原与草原的区别就在于城市。城市是什么呢?是人类文化、艺术、知识、财富的集合体。一座城市所能出产的财富是几万只牛羊都无法比拟的,而它所代表的人类最高级的思想,更是不可以黄金的价格来衡量……"
成吉思汗认真得倾听着这些对他来说都是前所未闻的事情。正像所有其他的蒙古人一样,他根本不懂什么城市经济,对城市经济没有任何概念;至少在他一生中的这个阶段,他还不知道除了把被攻陷的城市摧毁以外,还可以利用占领的城市做其他的事情。如果说父亲也速该与军师月忽难先后为他开启了对广大世界与伟大文明的认知之门的一角,使他得以管窥到其内的一缕春光的话,那么如今的耶律楚才则是以他那远胜于前两者的卓越才识,亲手为他洞开了这扇沉封已久的大门,使其中那无限明媚的春光乍然倾泄于他的面前,扑入他的怀中。
此后的三天内,成吉思汗便将楚材留在宫帐内通宵达旦得闭门倾谈,他下令除了吃饭时间外,任何人不得打扰他们。在这三天里,两个人都象着了魔一样,多半是在饥肠辘辘的情况下才会发现送入的饭菜已经冰凉;实在困倦了就随便斜靠在哪里打个盹。他们的外表开始憔悴,但都在彼此的目光之中看到了智慧与知识的火花。
在第三天的深夜里,成吉思汗向楚材询问起关于福兴之死的话题。楚材低下头想了想,回答道:
"这是汉文化对于执政者的一种要求。文死谏,武死战,国君死社稷,这是每个合格的君王与臣下都必须尽到的责任。文官在向君王进言的时候,要不避生死,实话实说;武将在为国作战时,也要有捐躯报国的觉悟;至于君王,则要将自己的生命与国家的兴亡牢固得维系在一起。只有这样,大家才可以同心协力,使国家内享安定繁荣,外御侵略之忧。"
成吉思汗仔细得品味着楚材的话,点头道:"你说的对,大家都要为这个国家尽责。象完颜旬那样抛弃中都的君主就是失职,而象福兴这样的人则是尽责。楚材,我希望你留在我的身边,为蒙古人讲出这些理道,使他们的心中也永远记住自己的责任,同时也随时解答我的疑问和提醒我对自身责任的遗漏,你肯吗?"
成吉思汗终于在最恰当的时刻说出了自己的最终目的,他以灼热的目光凝望着楚材的眼睛,这目光有洞辙对方肺腑的魔力。
楚材没有犹豫、没有沉吟、更没有丝毫停顿得回答道:
"愿效犬马之劳!"
"好!从今以后,蒙古人的队列中又多了一位乌托合撒儿(1)。"
一切不着痕迹,一切水到渠成。从此,一代天骄的身边多了一位富有良能的大臣。这位来自敌人营垒中的人以他那高尚的忠君情操、渊博的知识、出色的才干,赢得了成吉思汗的敬重与信任。当这一决定遭到许多重臣的置疑时,成吉思汗也不曾有丝毫动摇。他援引过去的往事来说服反对者们:
"收降伏为臣下,这也算一种危险吗?为我战死疆场的那些人之中,又有多少是最初追随于我的人呢?如果我的器量足够容纳别人,那么任何降伏者都将成为蒙古的箭簇!"
显然,这最后一句是在特指者别。
为了打消众人的疑虑,成吉思汗命楚材向众人展现他那高超的占卜之术。所谓占卜,就是牛羊的肩胛骨放入火堆中炙烤上一定时间后,再取出观察骨头上被火烧出的裂纹纹理,据此判断吉凶事。此前,在推举成吉思汗的大会上,那位通天巫曾经表演过,可见这种占卜方式在蒙古族中间相当流行。楚材的占卜结果,每次有非常灵验,很快便成为了蒙古军中不可或缺的人物。后来,每当远征之前便要请楚材来占卜吉凶胜负便成为了蒙古军中一条不成文的规定。
当然,楚材绝非有未卜先知之能的神仙。他的那些预言来自于丰富的学识、过人的才智和对人心的准确把握。同时,做为一名虔诚的佛教徒,他也有着悲天悯人的心肠。他准确地判断出成吉思汗绝非生性残暴的恶魔,他的那些破坏杀戮完全是源于对城市文明的不解,因此他决心借助神佛的名义来设法对成吉思汗施加影响,从而引导他走上文明之路,减少战争对平民的损失。
在成为大汗的谋臣之后,他就立刻提出了第一个请求:
"是否可以停止对城市的破坏和掠夺呢?我会证明,城市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它所给予大汗的回报,将会有百倍于掠夺的效果。"
"能试着谈谈这种效果吗?"成吉思汗问道。
"耕地是可以产出粮食的,而且产量一定会高于放牧。中原的财富,很大一部分都是来源于农耕,大汗若想要蒙古富强,完全可以让农民去耕种土地,然后向他们征收税款。这种税收将是源源不断,永远不会枯竭的宝库!"
"还有什么?"
"还有知识!知识有着改变命运的神奇功效。将有知识的人保护起来,再按照其特长安排到合理的岗位上,让他们去为大汗管理国家,那么民心将稳定,税收将增加!天下,可以在马背上得到,但是绝不能通过马背去治理!"
楚材的进言,无疑打动了成吉思汗的内心。在政治上,他有着超乎寻常的悟性,因此很快便感受到这些进言之中有着很大一部分可取的因素。也正是通过这些反复的磋商与交流,使得他愈来愈信服楚材的才智与品性。诚然,这种改变并非一朝一夕间就会产生立竿见影的成果,但是在楚材的力争与建议之下,许多野蛮的命令被改变了,确也是不争的事实。
与此同时,楚材也渐渐感受到成吉思汗身上那种非凡的魅力。从未有一位征服者会如此热情地听取被征服者的言论,并最大程度得去采纳其中可以理解的成份。即使这位主君与自己有着不可逾越的文化鸿沟,却并不妨碍彼此之间建立起一种互相信任的友好情感。至少,在楚材看来,历代王者之中能如此虚心听取不同意见的并不多见。他也就愈发坚信自己最初的选择是正确的。
根据楚材的建议,成吉思汗派人向先前派往中都负责处理战后事宜的三位部下传达了改变以往接收模式的新令谕:
金国士兵和一般市民以及中都城内所有的人,除战死者之外,全部集中到郊外的一个地方。对于这些俘虏,不再象从前那样首先挑选女人,将她们用绳索串连起来送往大本营。而是优先从男子中选出具有特殊技术和教养的人。
他还在令谕末尾严格告诫部下:对待这些男子不可感情用事,即使是抱有强烈敌对情绪的人,只要是有特殊技术和教养,一律送往自己的营地来。
接受到命令的失乞忽都忽一丝不苟得尊照执行起来。于是,连续多日之间,蒙古大营中就会出现这样一副无序循环的情景:
各种种族不同,打扮各异的人混杂在运送财帛的驮马队中走来。无论他们是顺从还是反抗,都不会遭到杀害,最多是被扭住胳膊,押回队列而已。在这样的行列之中,有最受欢迎的能工巧匠,有富于经验的武将士兵,还有一些稀奇古怪的出家人、占卜师、医生、法官、农夫和儒生。对于最后一种人,成吉思汗完全不知道他们的用处,只是命令由楚材来接待。
很快的,成吉思汗发现了一个要命的问题,那位终于职守的六弟居然真的没有送来任何一名年轻妇女。有的只是一些上了年纪的老妇,这自然不对成吉思汗的胃口。
"这些老太太是干嘛的?"
成吉思汗向解送者询问道。
"据说是产婆,懂得怎样顺利的接生孩子。"怯薛歹们回答。
成吉思汗的眼前立刻浮现出失乞忽都忽那张刻写着一丝不苟的面容,严肃、冷静得近乎淡漠的表情。
"真是哭笑不得啊。"
他这样想着,轻轻摇了摇头。然则,对于这种行为,他并不排斥,尤其是念及此前不久有人向自己汇报的那件贿赂案中这位"六弟"所表现出的廉洁操守,他的脸上又浮现起一丝欣慰。
事情就发生在三人察点府库的时候。负责镇守府库的是一位名叫合答的降将,为了讨好这三位蒙古将官,他取了几件绣金丝织品作为个人战利品赠送给他们三人。这种绣金丝织品相当名贵,那个世纪末,马可.波罗曾对这种织品赞叹不已。阿儿孩和汪古儿为这种名贵织品所吸引,便收下了礼物,唯有失乞忽都忽严辞拒绝:
"过去,这里的一切都属于阿勒坛汗;如今,这些都归于成吉思汗。你有什么权力擅自支配属于成吉思汗的财产?又怎敢擅取此物来送与我?我决不接受此物!"
通过这件事,成吉思汗深切得感到一种叫做腐败的文明副产物凭籍着人类性格之中的贪欲之心。三位使者之中的两位都受到了腐蚀,这就足以证明这种副产物的可怕之处,它正在逐步侵蚀着蒙古狼们的心灵,进而控制他们的精神,弱化他们的斗志。这种潜移默化的改变实在是比战场上面对敌人的百万大军更为凶险难防。
这位一代天骄在大胜之后,首先想到的不是弹冠相庆,而是找出自己的国家与军队之中还存在着哪些不足,又如何使之得以补完加强。他打定主意,一定要严厉惩罚行贿与受贿者,更要大张旗鼓得褒奖识大体、慎职守的忠诚之士,要让全体蒙古人都以失乞忽都忽为凯模,学习他廉洁自律的美德,更加忠诚于自己,忠诚于大蒙古的事业,而不至走上阿勒坛汗的败亡之路!
对于苟延残喘于黄河之南的金国,成吉思汗准备充分利用攻陷北京所造成的有利形势,一鼓作气得将其消灭,但那条叫做黄河的大河对于骑兵来说过于宽阔了,也是短时间内无法超越的一条天堑。虽然在征伐西夏时,他曾经见过这条河的上游,但是看到下游的时候,他还是无法将这两者统一起来。这条河在此地如同被天神的巨斧突然劈开一般,不可思议得向两边阔展出许多。而那湍急的河水,即使看上一阵都会令人的头晕目眩。
就如何通过黄河的问题,成吉思汗召开了军议。他特别征询了郭宝玉与耶律楚材的意见,二人都指出现在渡河作战是不可行的,因为难以短期内征集到足够的船只来运渡大军。若以小股部队进攻,则很难占到便宜。真正的大规模渡河作战只能等到冬天黄河结冰的时候才能展开,那时战马可踏过冰面进攻敌人。成吉思汗对此深以为然。他命楚材进行占卜,以确定未来的进军方向。楚材拿起被火焚烧过的羊骨,仔细观察上面的裂纹,然后抬起头来说道:
"臣昨晚夜观天象,见那象征着战争的长庚星出现在西北的天幕上;现在又根据这块羊骨上显示出来的征兆看来,在那个方向正有一位大汗的宿仇在蠢蠢欲动。"
"西北?指的是哪里?哈剌契丹?"
"是的。"
"那金国怎么办?就任他们恢复起来吗?"
"不,大汗对金的战争不能停顿,但也不能操之过急。"楚材缓缓得说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金国如今虽然衰败,但余势未尽,依旧不可放松。大汗应派一员上将统领中原之兵,采取稳扎稳打的战术,步步为营,一点点得蚕食金国,令其不得休息……"
一名怯薛歹的疾奔而入打断了楚材的话语。他向成吉思汗汇报了来自蒙古的重要消息:——
已故塔阳汗的儿子,丧失了国家的王子屈出律已经流浪到了哈剌契丹国,并得到该国古儿汗直鲁古的收留并将女儿嫁予他。谁知此人得志即猖狂,突然袭击了他的岳父,夺占了整个国家,并与西方回教大国花拉子模结成反蒙古同盟。现在,他正发兵攻打成吉思汗在西域地区的两个盟友:阿儿思兰汗和回鹘部亦都护。前者已经遭其攻灭并杀害,后者的处境亦岌岌可危。他还在西辽国内强行推广自己所信奉的景教,大肆杀害回教徒,实行血腥统治。
"西方的战鼓真得响起来了!"成吉思汗大声道,"漏网的残敌正在对我们磨刀霍霍!我将回师蒙古,然后立刻出兵讨伐屈出律,定要将这条祸根一举斩断!"
"诺!"蒙古众将起立,齐声凛尊。
成吉思汗郑重得说道:"对阿勒坛汗的战争也不能中止。三合木,我命你率军迂回山西,当冬天之时,从黄河最窄的地方踏冰而过,进入陕西,再折而向东,直取南京(开封)!"
"诺!"
奉令的三木合把阿秃儿是蒙古军中的后起之秀。这位年轻的武将在这次中都攻略战中建立了卓越的武勋,任命他为攻击部队长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合身的铠甲紧紧贴在他那匀称的肢体上,益发显出精悍干练的刚阳之气。他用兵擅长快攻,手下的部队有着无坚不摧的攻击力,但在防守战上,则略嫌欠缺耐性和韧性。不过,做为突击部队,这样的缺陷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这是他首次以总大将的身份独当一面,因此在任务的沉重感之外更有着跃跃欲试的欢喜与渴望。因此,他在得到命令后立刻于翌日发兵西行,在翌年(纪元1216年至1217年)冬天强渡山、陕两省之间的黄河,出其不意地袭取了古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古代的长安,现在名叫西安的大城市。此后,他挥军从东进潼关,却在这座天然险隘面前遭到了强力阻击。
在渭水汇入黄河的河口地区,拔地而起的山峦群峰形成了天然的障碍,尤其是那座被称为中原五大名岳之一的华山,更是高不可攀。它与北面的黄河形成了一条狭窄的地峡,潼关就是建立于其中,号称难攻不落的关隘。
三木合把阿秃儿在攻关受挫的情况下不敢恋战,立刻转而向南,通过一条人迹罕至的小道绕过华山,直取另一著名的古都洛阳。然而,洛阳方面也有了森严的防御,使得他无隙可乘。为了防止遭到反包围,三木合放弃了攻城的打算,快速向南进发,进入嵩山山脉。这里的地形之险峻绝不稍逊于华山,却恰巧是金国河南防御阵线的一个漏洞。在经历了艰苦跋涉之后,突然出现在汝南平原上,并一举攻陷了汝州和密州(2)这两座城市。从这里出发向北,完全是坦荡如砥的冲击平原,快马奔行之下,毋需几日即可直薄金国的新都开封城下。
这是一次成功的迂回作战行动,充分展现了三木合灵活多变,大胆巧妙的指挥才能。然而,他在嵩山之中耗费的时间过于漫长,以至于给予金国军队充分的布防时间。各路勤王兵马齐聚都城之下,尤其以山东民兵花帽军最为强悍。他们不仅有作战的实力,更有满腔对蹂躏他们家园的蒙古军的痛恨。因此,他们士气高昂地列阵于开封之南二十公里处的杏花营,对三木合军展开了强力阻击。
眼见急切间难以战胜敌军,三木合果断地下达了退兵令。事实证明,他的决定是相当明智的。就在蒙古军刚刚向西退却后不久,数支金军从几个方向包抄而来,险些形成合围态势。
跳出包围圈的蒙古军不敢再在河南地区停留,他们飞快地向西北而去,来到了陕州(3)境内的黄河岸边。不甘心就此放过蒙古军的金军随后追击,试图在河边再度包围敌人。然而,当他们来到河边才发现,这支给他们带来极大麻烦的敌军已经踏过冰封雪冻的河面扬长而去。
当三木合把阿秃儿进行他那艰苦卓绝的千里作战之时,成吉思汗已经率领大军北归大漠。他的目光已经从南方的金国转向了另一个世界——阿勒坛山以西的广大的未知的世界……——
(1)蒙语,意为长髯公。
(2)汝州,今河南临汝;密州,今河南新密。
(3)陕州,今河南三门峡。